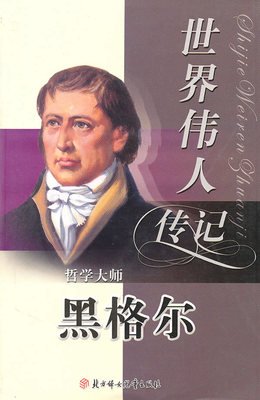《黑格尔导论》是一本由[英] 斯蒂芬·霍尔盖特(Stephen Houlgate)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5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个寓言,探究它成立的条件与适用范围尤其必要。霍盖特在本书中给出了有益的尝试。
霍盖特认为主奴辩证法的成立有两个条件:
2、非生死斗争。“黑格尔的主张不是说,历史上的所有这样的生死斗争都导致了支配与服从的关系.....”(p110)
霍盖特是对的,因为有死就没有主奴两方的存在,只有一方是构不成关系的,这也是科耶夫曾看到的。
但霍盖特也隐隐感到不妥,疑问是:没有生死主奴关系就能成立?因为没有生死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奴隶对主人的服从,主奴关系照样不成立。
于是霍盖特面对着如何处理"恐惧"这个烫手的山芋。他说“在黑格尔看来,恐惧的思想是一柄双刃剑。“ 霍盖特把皮球踢回给黑格尔。他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在恐惧中,自为之是就显现于奴隶自身之中“。(此句翻译更清楚的译法参见先刚版《精神现象学》124页)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奴隶因为认了命而找到自我身份的肯定,也知道了自己的否定面,从而有了自为的方向。
但是奴隶的自为仍然受到主人的制约,尽管他可以在主人力有未逮的领域大展拳脚,也可以希望山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但实际上却只能局限于修理地球、装修私室、老婆孩子热炕头等极有限的领域。而对被主人垄断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奴隶们只能像阿Q般抱怨。
因为很显然:恐惧会让人不”自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一节后接下来的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哀怨意识都是对不”自为“和”自为“过头的不自由的写照。而祈愿在主奴斗争中找回的自由却不见踪影。
恐惧与”自为“的之间关系尽管不是对应排斥性的,却是你增我减负相关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从主奴辩证法推理出自由的诞生表现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黑格尔的一厢情愿。
所幸的是黑格尔自由进程的脚步并不停留,可与恐惧抗衡的其他观念如良心等引导”自为“继续前行,直至制度化自由。
《黑格尔导论》读后感(二):摘要:P3-P310
3
黑格尔追随康德,强调我们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所有活动中都预设了范畴和概念。然而,他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康德。首先,由于对康德来说,我们带给经验的范畴是我们自己思想的产物,所以我们有权声称的就只是,我们根据这些范畴来理解世界。我们无权声称,世界自身是根据这些范畴建构起来的。康德认为,我们作为有理性的是者,不得不根据诸如原因与结果之类的范畴来组织我们的经验,并且我们所有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组织经验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经验到的有序世界就是客观的、实在的*;但是,我们无法知道世界自身可能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对于世界自身的本质,康德并不简单地就是个不可知论者。他非常强烈地暗示,它并不是根据我们的范畴组织起来的:我们通过范畴来理解世界,这些范畴容许我们按照我们特有的种观点看世界,但它们不容许我们把透过它们看到的事物视为事物的真实面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走到下述观点,显然不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后来尼采就采取了这个观点: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是由人的解释或虚构一层一层地累积而成的。
4
对于黑格尔来说,我们的范畴并没有使我们与事物的结构相隔膜;相反,它们恰恰是使我们走向事物结构的前提。我们的范畴并没有把我们限制在所谓人类经验的界限之内;它们装备了我们,使我们看到并理解了是者。我们来到世界,预先就被我们的理性和知性安排好了,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它。但我们的概念、范畴结构与世界自身的结构是同一的,从而,它也揭示了世界自身的结构,因为我们自己就生于我们遭遇到的这个世界之中,因而也享有它的特性。这不是说,我们做出的所有特殊判断——例如因果关联判断—一全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说,我们对因果性所蕴含的东西有一个完全的构想。不过,它的确意味着,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因果性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构成特点,它不只是我们“强加”给事物的一个概念。
因此,黑格尔同意康德的是,把范畴施加于我们感知到的世界;但不同于康德的是,他认为,那些范畴使有关世界自身的真正知识得以可能,它们绝不只是给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类经验带来秩序。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智为有关事物的真理做了概念上的准备,我们才能够获得通向那一真理的进路。真理绝不是简单地向我们涌现出来,我们必须以正确的心智架构走向真理。如果真理要从根本上被我们认识,我们就必须自己主动地显明。
黑格尔与康德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同样是根本性的,它涉及历史的问题。对康德来说,我们通过一个概念框架理解世界,这个概念框架是作为有理性者的我们特有的,它没有给予我们通达事物“自身”的任何进路。然而,那个框架对于所有有限的有理性者来说都是固定的、普遍的。它构成了不变的、永恒的坐标格,给予人类经验一个统一的概念结构。不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或许提出了有关世界的不同理论,但在康德看来,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用以开展工作的人类知性的基础性范畴——诸如单一性、多数性、可能性或必然性—在整个历史上一直都是固定不变的。亚里士多德构思它们的方式与康德自己构思它们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5
在黑格尔看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某些范畴——例如,是(being)—很有可能是普遍的;不过,根据他的看法,其他的一些范畴,例如原因和结果( cause and effect)、力与表现( force and expression),只有在一些比较高级的文化中才会被发现。此外,所有的概念一普遍的概念和不普遍的概念都是被不同时代、诸多文明以不同的方式构思和理解的。思想的范畴不是贯穿历史岿然不变的固定的、永恒的形式,而是其含义在历史中有所变更的概念。对于康德来说,范畴构成了知识永恒的先验框架,而对黑格尔来说,它们则构成了知识变化着的历史性的前提。
11
我们要注意,黑格尔的观点不同于卡尔·马克思作品中的观点,然有时候人们认为它们是类似的。马克思—至少在我发现对他的想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之中0—把技术的变化,物质生产力中的变化视为历史中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信仰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这样的技术变化的产物。然而,在黑格尔看来,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它的一般特性或“精神”,一种文化或社会的技术力量的发展本身源于这个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特性。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文明对技术革新—例如印刷术,它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多次被发明——做出了不同运用的原因。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的中国人知道许多事情,那个时候欧洲人还没有发现它们呢,但是他们不明白如何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例如指南针和印刷术…还有火药,他们声称在欧洲人之前发明了它们,但他们的第一批大炮还是耶稣会教士给他们造的。
黑格尔并不是主张,文明史的每个细节都可以根据文明的一般特性进行解释。要确立是什么导致了一个社会中特定事物的诞生,需要特定的历史学的或社会学的研究:这样的事物不能够根据关于文明性质的一般理论做出解释。然而,黑格尔认为,在文明史内部所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互动中,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那个文明的基本特性。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在一个文明中要辨认的最重要东西不是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事件或成就,而是根本性的精神,它使得那个文明成为它之所是。
47
思维无( thinking of nothing)并不简单地就等于不思维( not thinking)。思想悬置了它的所有预设,从而最终不思维任何特定的东西,但它依然是思想,虽然是完全无规定的、尚未展开的思想。因此,虽然当我们思维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思维无(无论它是什么),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依然在思维。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无(无论它是什么)正是我们所思维的东西。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纯然的、完全的无对思想来说实际上有着它自身的直接性:纯然的无被思想确切地理解为是无,而不是其他某个东西。然而这意味着,纯然的、完全的无事实上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因为当我们思维无的时候,我们必定是在思维纯然的无规定性,这个无规定性纯粹仅仅就是它所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思维空洞的、无规定的是着的东西(be-ing)。因此,正如对纯然无规定的是的思想滑入了对无的思想,对无的思想也必然地滑入了对是的思想。
50
黑格尔的逻辑没有把我们带入概念的混沌之中。它也没有把我们带向如下头脑简单的实证主义结论,即“是”这个语词根本不意味任何东西,我们不妨抛弃它。最后,它也没有把我们带入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主张,既然是是无,因而只有无才是是。黑格尔无预设的逻辑把我们带向了如下这个悖论性的思想:无本身就要被思维为是,就是说,要被思维为非一是(non- being)或不一是( not-being),而且也只能够被思维为不是它不是的东西( not being what it is not)请注意,无在逻辑上转变为“不一是”(not- being, Nichtsein),因面是与是(是本身被定义为不是它不是的东西)无法区分的。因此,说是与无是无法区分的,这同时也就是在说,是( being)与不一是(not- being)是无法区分的。然而,正是这个令人困惑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把是与不是之间的差异—在这两个术语无法区分这个思想中,依然无法消除地蕴含着这个差异思维为一个有规定的差异。
53
黑格尔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自由地、自我批判地规定思想的范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思想能够也必定会发展出更加复杂的范畴,以解决出现的矛盾。因此,如黑格尔所构想的,思想不能简单地避免矛盾,或者—像罗素那样—总是把矛盾看作错误的一个标志。相反,思想必须考虑它的范畴中蕴含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因而,黑格尔逻辑学中最高级的范畴将会是这样一些范畴,在这些范畴之中,矛盾得到了最明确的呈现,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54
在《逻辑学》余下的部分,黑格尔将会尝试着从我们刚才考察的对空洞的规定性的思想推导出更进一步的范畴。那些范畴将会呈现出所谓有规定的东西进一步的规定性,将会表明,规定性在于质、量、特殊性、形式、内容、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范畴。我这里列出的只是黑格尔逐步展开的诸多范畴中的少数几个。在《逻辑学》的最后一部分“主观的”逻辑或概念的逻辑,我们清楚了,规定性在于具备一个概念的或合理性的结构。因此,正是在这个部分中,思想最终不仅把它的范畴认作有规定的是的诸规定,同时也把它们认作思想的诸规定。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无预设的思想已经现实地成为了它曾经潜在地是的东西,也就是说,无预设的思想通过对它自身的思想成为了规定性。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逻辑学》的最后一个概念是自我规定着的理性自身这个概念,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理念”。当我们到达了那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无预设的思想最终确定了,它的根本特性在哪里。
57
在康德看来,分析揭示了概念之间的直接同一性关系或相等关系:单身汉等于未婚男人,原因等于造成结果的东西。然而,黑格尔则不认为,是这个概念等于变易这个概念。他认为的是,当我们考虑是这个概念时,它变成了变易这个概念。黑格尔的逻辑学仅仅显明了最初的范畴中蕴含的或尚未被思维的东西,就此而言,它是“分析的”。然而,通过显明是这个无规定的范畴,我们并非仅仅只是用不同的语词重述明显“包含”在该范畴中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范畴出现了。范畴转变为新的范畴,正是这一点使得黑格尔逻辑学的发展并非直接就是分析的。
黑格尔的“分析”方法不同于康德的分析,它要求我们对我们思维的方式进行不断的、微妙的修正。最初,我们认为,思维是( to think being)简单地就是思维是,但在逻辑学的进程中,我们最终明白了,思维是乃是思维变易、质、量、特殊性、本质与实存、实体与因果性,最终是思维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本身。所有新的规定性都源于之前的规定性,都会改进我们最初对是的思想。所有这些新的规定性都会在两个意义上揭示出之前规定性的真理:它会明确地展示出之前的范畴所暗含的但也遮蔽了的东西,它会揭示出之前范畴自身的局限。由此,黑格尔的逻辑科学规定了思想的恰切范畴,同时也对那些范畴作出了限定。例如,它确立了我们如下做法的正确性:探究某个东西的根据,而不是单纯地接受它是这个事实;但它也揭示了,某个东西的真正根据并不是另外的东西,而是那个东西自身的本质,或是使得这个东西成为其所是的合理性概念。
对是的思想的绝对真理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思维是的时候,思想乃是在思维理性本身的自我规定性,这个绝对真理只有在进程的终点才变得完全明晰。黑格尔纯粹概念分析的“圆圈”在这一点上才得以完成,在开端未被思考的东西被完全明晰地揭示了出来。
63
思考和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实际上还有他哲学的其他部分),就是理解辩证思维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是寻找结论(虽然那个辩证的过程得出了结论)。它要理解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凭借着这个过程,一个范畴(例如是)转变为下一个范畴(例如有规定的是),要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放弃一个范畸最初的规定性,允许那个范畴的一个更加精微的规定性出现。但我们也要能够保持对这个最初范畴的考虑,把它视为那更复杂规定性升起的源头。我们必须要始终认识到,有规定的是这个范畸是纯是这个范畴的一个更加精微、更加真实的规定性。实际上,其后的所有范畴都是这个最初的,表面上简单的对是的思想更加精微、更加真实的规定性。我们要时刻牢记思想由之开端的这个最初的概念,我们只有通过这么做,才能把据到如下事实:概念(例如是)发展和产生出了一个逻辑的“历史”。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范的逻辑起源,注意到它自身的规定性以及它使自身转变为一个新范的那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以黑格尔的方式理解一个范向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对于黑格尔来说,“真理是它自身的自我运动面他希望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那个运动,那么,对于阅读黑格尔的文本我们就用不着感到限惧了。
78
黑格尔不是通过显明我们如何终究能够通达是的领域(怀疑主义认为我们不能通达这个领域),而是通过把怀疑主义所立足的这个对“是”的构想(是可能不同于思)拒斥为无根据的—一至少在最初是无根据的—来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的。
对于黑格尔来说,开始无预设的是态一逻辑学(onto-lgio)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只需要这样一个自由的意愿,愿意悬置我们所钟爱的那些有关是与思的预设,愿意从对是本身的空洞之思出发。
84
此外,他还注意到,意识以两种方式看待它的对象:种是把对象视作自在的( in itself),一种是把对象视作为意识所认识的—是为了(for)意识的意识自发地把自己区别于某个东西,同时又把自己与它关联起来,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个东西为意识而实存;这一关联的确定方面,或某个东西为意识的是的确定方面,就是认识。不过我们把这个为他的是( being-for- another)与自在的是( being-in- itself)区别开来;与知识或认识相关的东西也区别于这个为他的是,它被设定为实存于这一关联之外;这个自在的是就被称为真。
这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的意识对象:自在的对象( the object in itself)和被认识的对象( the objeet known)。只有一个对象,只不过意识区分了它将之作为对象本身所是的东西和它实际上认识或经验那个对象的方式。此外,意识自身也能够确定,它对于有关对象的知识或经验是否真的与它认为的自在对象的所是相符合:
因为意识一方面是对于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它自身的意识;既是对于对它来说为真( the True)的意识,又是对于它关于该真的知识的意识。既然两者都是为了这同个意识的,所以这个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关于对象的知识是否符合这个对象,这是由同一个意识来认识的。
109
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主要专注于它自己。不过它也依然意识到了不同于它自己的东西,它的自我确定性是以与它相关联的其他事物和其他自我为中介的。黑格尔论说道,这样的中介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方面,自我意识通过否定对象的独立性,迫使它们服务于自我—就是说,通过把它们转变为满足欲求的手段—来肯定它对自己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发现,它的身份得到了另一个自我意识的肯定,这后一个自我意识通过把自己的关切抛在一旁,对前一个自我意识给予承认而“否定了它自己”
110
黑格尔在他对主-奴关系作出的著名阐述中表明,每个自我意识都通过它自己的经验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它最初以为自己是的东西的对立面。主人认为他自己显示了无拘无束的“否定性”或欲求的自由和力量,但他后来认识到,他的自由事实上依赖于奴隶的劳动和服侍。相反,奴隶认为自己是完全不自由的,不过后来他认识到,他事实上在自己的被奴役状态中享有真正的自由。
113
奴隶看到他自己的自由体现在他的劳动对象之中。他作用于对象,赋予它一个新的形式,把这个形式视为在对象自身中展示了他自己的自由活动。以此方式,“劳动者的意识最终在[对象的]独立之是中看到了它自己的独立性”。2不过,奴隶继续把对象视为不同于意识的东西,当然,奴隶也把它视为一个缺乏意识、自我或它自己的自由的无生命对象。他把主人视为另一个“自为的是者”,不过他并不以此方式看待他劳动的对象。因此,他没有把他自己的自我视为复现于另一个自我意识之中,相反,他把自己的自由视为体现于“他所造就的物的形式之中”。2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在奴隶与其对象的关系之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奴隶在他赋予对象的形式中发现了自己作为自我意识和自为的是者的身份。用黑格尔的话来讲,“形式和自为的是者不论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就它们自己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现在就过渡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明确地接受了奴隶的经验中所揭示出来的真理。
124
因此,意识通过逻辑地转变为理性,朝着向绝对认识的转变迈出了更深入的一步。简单的意识主要指向其对象,它把它们视为直接地被给予的东西(这个、这里、这时),再把它们视为具有各种属性的统一的事物,继而又把它们视为受着内在的力和规律支配的对象。然后,自我意识通过否定这样的对象而与它自己相关。接着,理性则通过发现自已隐含地呈现于世界本身—“先前,它只关切于这个世界的暂时性现在,它则关切于它的持存性”4“——之中而与它自己相关。因此,理性可以说是把自我意识主观的自我确定性和意识的客观确定性的特合而为一了。它把它自己理解为是内在于另外一个东西之中的,它承认,这个另外的东西不同于它自己。
理性与斯多葛主义的主要区别正在于此。与斯多葛主义一样的是,理性也意识到了它自己和它周围世界的同一性:它意识到,“自我意识和是有着同样的本质”。但不同于斯多葛主义的是,理性并不是简单地回退到它自身之中,以发现那些阐明了事物之真正本性的概念;相反,理性也注意世界本身,它发现理性就隐含于它所遭遇到的对象和个体性之中。因而,当斯多葛主义与所有的自我意识(奴隶除外)一样,主要地关切于它自己以及它自己的思想时,“理性……则在世界之中有着广泛的关切,因为它确知自己呈现在了世界之中,或者,向它呈现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当黑格尔把理性的立场等同于“观念论"( idealism)的立场时,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观念论并没有把世界归约为自我的单纯“投射”或反思,而是肯定了世界本身独立的实存及其隐含的合理性。对于黑格尔来说,真正的观念论不同于主观的观念论,前者认识到,世界有着一个合乎理性的、因而“观念化的”结构。
125
然而,理性依然缺乏绝对的认识。这是因为,它依然太过狭隘地专于它认为隐含地合乎理性的直接个体性—自然对象的个体性以及自我意识自身的个体性。实际上,这也是理性采取了“颅相学”这个看起来非理性形式的原因,在颅相学里,合理性的自我意识相信,它能够在个体颅骨的隆起和凹陷中发现具(备形)体的理性,以及“内心的规律”,理性把这种规律等同于个体内心的各种直接感受。然而,理性被它自己的经验驱使着,转变为一种更深入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认识到,它自己就是现实地普遍的理性,它认识到与之相关的他者也是意识到自身的普遍理性:“最初,……行动的理性意识到它自己仅仅只是一个个体( Individuum)………,然而,随后,它的意识把它自己提升到了普遍性,它就变成了普遍的理性,并意识到它自己就是理性,就是一种已经自在自为地得到承认的意识”。这样自觉的普遍理性一一它也把它的他者承认为自觉的普遍理性—就是精神(Geis)。
127
黑格尔对精神的各种形态的说明异常丰富,这里我也不打算公允地对待它们。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精神不是仅仅停留于一个伦理的世界,它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关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抽象知识( Ir issen)w也就是说,它变得更加明确地自觉。意识得到这样的提升,其最初的后果是导致精神分裂为二,从而变得分裂或“异己”。特别是,它分别落于一个客观地实存的世界(教养[ Bildung的领域)以及“纯粹意识的领域,后者超越了前者,它不是一个当下的现实性,而仅仅只为信仰而实存”。不过,最终精神在自身之中克服了这一分裂。它是在黑格尔所谓的“绝对自由”这种意识形态中开始做到这一点的。
这种形态是精神的一种真正的形态,因为它认识到,自己明确地就是普遍的理性。不过,它首先主要地并不是在法律和习俗公共的、具体的形式中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理性的,而是在纯粹思想、纯粹理性以及纯粹合乎理性的意志这样一种更加抽象的形式中认识到这一点的。这会被视为一种真正地合乎理性的意志,因为它认识到它的原则不仅是它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是客观地、独立地有效的、有权威的。此外,这种自由的、自觉的精神不像斯多葛主义或怀疑主义那样,从世界回退出去,或是把自己禁闭于它自己牢不可破的自由之中。相反,这种精神认识到,它自己以及它自己的自我确定性就构成了精神性的现实性本身,或者说,就是精神性的现实性自身的“本质”。也就是说,它认识到,它与之相关的具体的、精神性的共同体是由纯粹理性所产生和维系的,而它又知道,它自己就是这个纯粹理性。
132
黑格尔在这里所考察的道德意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意识,它类似于(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描述的道德意识。”这样的道德意识把自己视为只受到纯粹义务观念的约束。实际上,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意识,它所关注的始终是尊重和符合纯粹的、普遍的义务本身的要求,它不相信,义务的观念本身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捍卫不同的特殊义务。
这种抽象的道德意识把义务理解为是由它自己自觉的理性加之于它的;它把这样的义务视为不仅是一个沉思的对象,还是一个应该指引我们在世界之中行动的东西。此外,义务也被理解为是针对这样一个世界的:该世界由于其本性,对于义务的要求漠不关心,也达不到义务的要求。这个世界—它不是它应该是的模样——不仅包括我们周围的对象和人群,还包括道德行动者们自己的自然本能和性情。这样,道德的意识必定会以义务的名义把自己理解为是与自己自私的方面相敌对的,因而,它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一种“否定性的本质,对于它的纯粹义务来说,感性只有一种否定性的意义,只是一种不符合义务的东西”。
133
道德的意识也设定了它自己之外的另一个意识,或是构造了该意的形象或表象( Vorstellung)。道德的意识设定这另一个意识,是为了捍卫或“神圣化”( heiligen)世界之中各种特殊的、确定的义务。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道德的意识认为它有责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纯粹的、普遍的义务。不过,这样的意识也承认,我们在世界之中会遭遇到许多不同的、特殊的情形。就道德的意识而言,问题在于,在义务本身的观念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在特定的情形下被要求施行一而在别的情形下则不要求施行的那些特殊义务是正当的。例如,单独的义务可能会要求,我们尊重其他合乎理性的是者,但它不能确立起个规则: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应该贸然去拜访我们的邻居,以示我们的友谊;而在其他一些情形下,我们则应该弃他们于不顾,以保护他们的隐私。此外,一个特定的行动方式在某些情形下通常被视为正当,因而被视为特定义务的地方,道德的意识不能够在它自己对普遍义务的理解中找到任何根据,从而把那个特殊的义务视为神圣的。它自己的道德理解仅仅要求它确保,这样一些特殊的“义务”与义务本身的普遍要求不相冲突:“对于那众多的义务,道德的意识本身在它们中间只留意那纯粹的义务;那众多的义务作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是特定的,因此它们本身对于道德的意识来说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135
因此,道德的意识最初说是克服了精神从其自身的异化,但现在它被证明在自身中是分裂的。一方面,它相信自己的自然性情阻止了它完全地按照义务去行动;另一方面,它知道自己的纯粹意志依然是真正地道德的。不过,道德的意识并没有简单地回复为自我异化的:因为它把自己道德的不完善和完善理解为处于持久的统一之中的,它们是同个意识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它认识到了义务的至上性,并设定了一个超出它自己及它自己的不完善性的神圣者,并努力达到这个神圣者;就此而言,它把它自己不完善地道德的自我理解成了真正地道德的( genuinely moral)。
137
通过注意到处于它自己的道德立场之中的那个伪善,意识指出了以下事实:只有在义务和现实性之间的这个根本的对立被放弃了的时候,才能达致真正的道德。真正道德的意识不会令义务和现实陷于对立,不会去追求那个它认为不可能的任务—使它的行动符合义务,相反,真正道德的意识的行动和自然性情现实地就符合义务,现实地就是道德的。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其道德品格置于其行动和义务现实的和谐之中的,乃是良心( Gewissen)。
138
显然,黑格尔相信,良心要比抽象的道德意识更完全地体现了真正道德的精神。不过,在精神的逻辑发展中,良心依然没有代表最后的阶段,而是会由于它自己经验的要求,转变为一种更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宗教。良心的问题在于:虽然它避免了道德的意识的伪善,把真实的道德置于具体的道德行动之中,而不是置于虽有良好意图却没有任何效果的“善良意志”之中,然而,它相信,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道德的,只要它充满道德自信地去做它们。因此,它就把真正道德的行为与任何它碰巧—满怀良心地—在做的行为等同起来,从而实际上就把真正道德的生命和它自己直接的、偶然的实存混在了一起:“在它自己眼里,处于偶然性中的它自己是完全有效的,它知道它直接的个体性就是纯粹的认识与行动,就是真正的实在与和谐”。结果,它被证明是一个完全不可亵渎的意识,这个意识相信,既然它的意识是善的,它就不可能做出任何错事。当然,在一个对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假定,这样自我宣称的道德神圣性对于精神来说是成问题的或是不恰当的,黑格尔就没有这么做。不过,黑格尔表明了:良心通过内在地转变为宗教的立场,摧毁了它自己处于绝对状态这个宣称。不过这还言之过早。让我们回到黑格尔对良心的说明的起点。
139
黑格尔由之出发的地方是:良心把道德的行动和它自己自觉的活动等同起来,从而把它自己视为充分地体现着道德的生命。然而,良心拒斥道德的意识的立场,后者断定自己的行动与义务的一个明确的标准相对立。因此,良心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把它的行为与这样一个明确的标准相比照,并通过这个明确的比照来得出结论说,它们们是道德的。相反,它直接地就知道它的行为符合义务。此外,它在自身之中直接地就知道,在某个给定的情形下它的义务是什么。因此,良心是完全地自我证明着的( self-certifying)道德意识:它既直接地在自身之内就知道,怎么做才算是道德地行动;又直接地看到,它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是道德的。
140
实际上,对于良心说,不可能再有其他共同的道德标准了。良心拒绝乞助于一个独立的公共的道德判断标准(所有的道德行动都要符合于它),而是坚持认为它直接就知道,它在所有个别情况下的那些行动都是义务所要求的不过,在缺乏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各种道德行动唯一共有物特征就是如下事实,它们在得到实施的时候都抱有它们是道德的这个确信。因而,对于良心来说,道德的行动就是这样的行动,它适应个的情形,其行动者确信,他们是在做着正当的事情。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行动、义务的本质在于良心对它的确信;…它的义务在于它对又务的纯粹确信”。
153
然而,随着行动者和判官内心发生了变化,道德的意识或精神对它自己与理性或真理之间的关系最终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这样的意识依然认为自己是道德的或神圣的;但它只是在自己不再仅仅只是它自己的情况下,才把自己视为神圣的。这就是说,它把自己的道德“完善性”或“神圣性”置于它如下的行动之中:它舍弃了自己孤立的邪恶的或硬心肠的—自我,从而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身份。这样一种交往乃是基于宽恕与和解的语词和行动之上的。因此,用劳厄的话说,对于真正道德的良心来说,宽恕与和解构成了“人的神圣之维”。或者,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那和解性的‘是的,两个‘我'在其中都舍弃了各自相对立的实存—就是我’的实存,它已经扩展为一种二元性,但又在其中与自身保持着一种同一性……:它就是在以纯粹知识的形式认识自己的那些人中间得到了体现的上帝”。抽象地道德的良心把它的“神圣性”理解为存在于它对自己和自己之称义的直接确定性之中。相反,真正道德的良心则把它的神圣性置于它与其他人的友谊和相互承认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就它是处于绝对对立之中的它自己的普遍知识”而言,它认为自己是神圣的。
154
接受了这种新的“神圣性”或绝对理性观念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对于黑格尔来说,真正宗教的意识因而就不是自我称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并不认为,它的道德“纯粹性”使它与其他“罪人”分别开来了,予了它由于其他人的罪恶而断然诅咒它们的权利。真正宗教的意识对于伪善和邪恶经常出现的可能性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意识,但它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宽恕的、爱的意识,寻求与其他人和解。正如黑格尔所坚持认为的,它是一种“宽恕邪恶”(当那颗邪恶的灵魂忏悔和悔改的时候)的意识,“它在这么做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简单的、单一的本性96和严格的不变性”。换言之,真正的宗教意识不是把神圣性仅仅置于它自己(以及它自己的称义感或不可能判断错误这种感觉)之中,而是把神圣性置于这样一种自我之中,该自我舍弃了自己,在它与其他人的友谊之中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自我。实际上,宗教的意识之所以出现在《精神现象学》之中,仅仅是因为,两种意识形态舍弃了它们自己。
苦恼的意识通过舍弃它异化的自我意识,把“不变者”或普遍者的意志迎入自身之中,首先转变为理性。后来,道德的良心舍弃它与普遍理性直接的同一性,转变为宗教。因此,真正的宗教意识既不是一种苦恼的意识,认为自己与真理断了关联,也不是一种自我称义的意识,认为它单独地就体现了精神。真正的宗教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它发现,真理一一绝对理性或“上帝”一就体现在它与其他人的交往之中。
164-165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本章和第三章中触及的那些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黑格尔所追踪的发展有着一个清晰的结构,黑格尔首先考虑的意识本身,它专注于对象或不同于自我的东西。随后,意识转变成了自我意识,它专注于它自己,并把它自己理解为对不同于它的东西的否定。因面自我意识自己转变成了理性,理性看到了,他者本身是隐含地合乎理性的,就此面言,理性看到了自我与它的他者之间一种隐含的统一性。因面,理性变成了精神,精神的对象是明确地而不是隐含地—一合平理性的,并且,对精神而言,这样的合理性或理性是明确地普遍的。这样的精神把它自己以及它的他者都理解为自觉的理性,因此精神涉及它视为一个普遍理性的世界(例如,法律和习俗的伦理世界)。
不过,随着精神作为合乎理性的精神,对它自己变得越来越自觉它也变得异于自觉的普遍理性的世界。后来,精神通过把自己理解为有责任(铜鼓革命性的自由)创造出自觉的理性的世界,弥合了这一裂隙。不过,这样“革命性的”精神的致命经验使它把它自己的纯粹自我视为普遍理性唯一真实的现实化。在这个地方,精神一处于道德神和良心的形式之中一把普遍的理性与它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因而也把它的对象和它自己合并在一起了)。
当精神学会了舍弃它自己,并在忏悔、宽恕与和解中认识到了它自的绝对合理性和“神圣性”,精神的倒数第二次转型就发生了。在这地方,道德的精神转变成为宗教。使得宗教与道德良心区别开的,根本说来乃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依然非常重要。良心把它理解为自觉的普遍理性,而宗教则把它自己理解为已经对自己变得自觉的普遍理性。换言之,宗教认识到—一在某种程度上良心则没有认识到——普遍的理性与人的自我意识并非是完全一样的,它是在人之中变得自觉的真正绝对的是。宗教把这一绝对的是或理性表象为“上帝”,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它非常强调这样绝对的是与人之间的差异。不过,与此同时,在道成肉身和圣灵的教义中,宗教又据示出,上帝实际上就是变得与人合而为一的过程。
哲学,或绝对认识,是精神的这样一种形态,它接受了隐含于宗教之中的真理。它认识到,绝对的理性不是与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无限的他者,而是作为人而变得自觉的是本身(唯一的现实性)。对于哲学而言,在是或绝对的理性与人的自我意识之间依然存在一个差异,因为前者并不能被归约为后者,而是也呈现为自然这种形式。不过,哲学也认识到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并且把它们视为构成了同一种现实性。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一点。一方面,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哲学认为,人无非是已经变得自觉的是。另一方面,哲学也把是理解为与自觉的思想有着同一种逻辑形式,即“概念”这种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在《逻辑学》里得到了阐明)。因此,在哲学的思想中,意识的两个方面最终都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因为,思想与不可被归约为思想的绝对的是在此意义上,绝对的是不同于思想—关联着,但思想与绝对的是在形式上又是同一的,因而思想能够在绝对的是之中认识它自己。换言之,哲学的思想或绝对的认识是“在绝对他者中的纯粹的自我认识。
167
当然,思辨哲学本身也是批判性的。它展示了:是不可能仅仅被理解为“是”或“本质”,而是必须也要被构想为“理念”;自然不能够仅仅只被理解为空间、时间和物质,而是必须也要被理解为包含了有机生命;人的精神不能够仅仅被归约为个体的主观性和激情,而是必须也要采取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宗教的交互主体性这些形式。不过,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出它所考察的诸范畴以及自然和精神的诸形式所具有的持久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现象,例如疯狂、奴役、不公正和邪恶,被显明是必然的,但只有当人的精神固执于一种特定的立场的时候,这些现象才会被揭示为在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其他情况下哲学展示了,得到考察的那些现象——不论它是习惯、语言、国家、艺术抑或宗教——对于人的自由来说是根本性的。因此,哲学乃是一门更加肯定性的学科,其目标是要揭示出是、自然以及人的自由之中固有的合理性,而现象学则可以说是更加“怀疑性的”和解构性的。
我认为,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这一差异在这两门学科对宗教的处理中得到了反映。正如我在第十章里边论说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证明了,对于人类对真理的完整经验而言,宗教是绝对必需的,但宗教精神仅仅表象和感受真理,这个事实表明了宗教精神的局限。尽管如此,宗教也表明,它对于完整的人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虽然哲学概念给了我们对真理最明晰、最充分的理解,但我们不能够仅仅以概念为生,我们也需要满足情感和想象的需要(正如我们在艺术中满足直观的需要一样)。因此,哲学通过展示出宗教是对真理感受性的、形象化的意识,肯定了宗教对于人类个体和社会极端的重要性。
168
因此,在《精神现象学》和柏林《宗教哲学讲演录》之间,黑格尔对宗教的处理的确发生了一个细微的变化。在前者那里,哲学或绝对认识实际上的确超越了宗教,而在后者那里,哲学则肯定和得卫了宗观点。“然而,这个差异绝不是由于黑格尔的什么日益增长的保守性它反映了现象学与哲学各自的方法和进程之间的基本差异,现象学的要点是要表明,意识的每一个形态都瓦解了自身,从而使得更进一多的那些形态成为了必然的。因而,对宗教的现象学处理明确地关注于宗教经验以何种方式为哲学铺就了通路,相比之下,哲学本身则留了,现象是如何通过是本身、自然以及人的自由而成为必然的,并且象如何就是它们。因此,对宗教的哲学处理强调的是,宗教是一种定全恰当的感受和表象真理的方式,从面,哲学肯定了宗教对我们生命久意义。但倘若我们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问做出选择的话,那么很是哲学的说明必须被赋予优先性,因为,哲学揭示了黑格尔所认为的有事物的终极真理,它包含了对真理的宗教经验的真理,另一方面,学并没有伪称揭示了有关宗教的终极真理,而是自身满足于不F数如何以及为什么使得对真理的哲学理解成为了必然。
271
动物绝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属或种的一员。一个动物所属的物种构成了那个个体的“实体”:它界定了该动物是哪一种生物。“然而,物种却不受制于一个个体(当然,除非这种动物处于灭绝的边缘)。它贯穿于多个个体,因而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动物生命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特定的物种或属把自身显示为明确地普遍的。
动物对于它们是同一个物种的成员这个事实没有任何明晰的、概念上的意识:它们没有把自己思考为一或者不知道自己是一猫或者狗。不过,它们在交配的时候显露出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这个感受对于黑格尔来说,动物的本能总是会强化它是它自身这个感受,“把它自己制造为一种自我感受,制造为总体性”。不过,动物在交配中与另一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时,“在这个他者中延续着自己,在这个他者中感受着它自己的自我”。因而交配给动物提供的东西也就是交互的承认给有意识的人提供的东西,即“只有在他者中才具有他们的自我感受”。”(当然,对于人来说,性关系与交互承认在婚姻制度中被结合在了一起。)在一个动物的生命中,这种在与另一个动物共处时是它自身的感受绝不是一个难得的或随意的额外东西。动物被一种强烈的相互需要驱使着去交配;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对另一个动物的需要和依赖惑隐藏着以下感受,动物感到它与另一个动物是同一类,感到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或“普遍的”东西。
272
只有当那个物种表明自己不依赖(因而独立于)特殊的个体,而是会在其他个体那里得到延续的时候,它才被证明是真正普遍的。在黑格尔看来,这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动物个体死亡了,而物种本身却继续活着,该动物物种才表明自己是真正地普遍的:“动物的]属或种仅仅通过[动物]个体的毁灭( Untergang)来保存自身
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动物是注定要死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有限的有机体,还因为它们是通过自己的死亡来保存和促进它们的物种(作为某个真正普遍的东西)的。黑格尔注意到,有些动物交配后立刻就会死亡。相反,更高等的动物“会活过繁殖活动,因为它们有一更高类型的独立性;它们的死亡是它们结构里边过程的顶点”。不在所有情况下,动物—包括人—在自身中都携带有“与生俱来的亡萌芽”(实际上,都具有患病的内在倾向)。动物的本性就是者后死去。
293
只有当意志不再依赖于某个被给予的东西时,这个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意志所意愿的东西不是被外在的或内在的偶然性所规定,而是被它自己所规定的时候,意志才使自己从这样的依赖性中摆脱了出来。但是,由自由意志自己规定的是什么“内容”呢?仅仅根据如下事实,即我是并且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会致力于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到意志在运用选择自由的时候试图保留和实现的东西,答案就变得很清楚了。当我们选择一个特殊的行为时我们明确地意愿着我们所选择的东西;然而,通过坚持我们没有被不可改变地束缚于它,我们展示出,我们所关切的不仅仅是这个特殊的选项,我们更关切于保留我们选择的自由。因此,无论我们致力于什么特定的事项,就我们寻求保留其他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而言,我们首要地关心的是保护和践行我们的自由本身。因此,任何自由的意志仅仅依据它是自由的而意愿的内容或“对象”无非就是它自己的自由。
当自由意志把它自身的自由当作其明确的对象而意愿时,它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意志,因为它意愿着一个“对于自我规定着的行动本身来说是内在的”内容,因而它并不依赖于一系列它被给予、以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内容。黑格尔告诉我们,“自由心灵的绝对目标(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叫它自由心灵的绝对冲动也好)就是,把自由作为它的对象。
296
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人作为自由的人而拥有的特定权利直接源于自由的人这个概念本身。这些权利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有权作为个得到承认的人而拥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被尊重为一个权利;也就是说,他有权利被视为一个权利拥有者。“绝对的权利乃是拥有权利[的权利]。”“当然,这个权利本身还没有确立对任何特定事物的权利,但它至少确立了,我有权利认为,我的人格和我被赋予广泛权利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这形成了黑格尔所认为的直接的或“抽象的”权利的首要命令:“成为一个人格并且也把其他人尊重为人格。”由于这个命令是纯粹形式的(因为它在一个人格的权利得到尊重的条件下,允许任何行为的发生),在现实中它就仅仅意味着如下的消极命令:“不要侵犯人格及其所蕴含的东西。”“结果就是,”黑格尔断定,“在权利的领域只有禁令,在这个领域中,如果我们考察其最根本的内容,任何命令的积极形式最终都是建立在禁令的基础上的。”
301
选择的自由被表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被表明依赖于特定的被给予的选项。现在,一个人直接的自由被表明是不充分的,因为承认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的这个人总是有可能不尊重它们,因而总是有可能侵犯其他人的权利。黑格尔认为,从这个不充分性得出的是,抽象的权利必定总是有被侵犯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即使权利必定要求直接的尊重,它也总是有可能需要得到强化,以对抗侵犯者,它需要通过对罪犯的惩罚来恢复自己的权威。
自由意志承认,自由是它必须意愿和尊重的的东西,但它认识到,它有能力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因而它明白,它需要不断地防备自己对自由可能作出的侵犯,这样的自由意志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道德的意志这样一个意志不仅仅把自由视为一个要求得到直接尊重的直接权利相反,它意识到,它必须坚持对自由的尊重,实际上一由于它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它必须自己持守对自由的尊重。因此,道德的意志将会认识到,它必须使自己尊重自由,它必须承担起促进自由的责任。
此外,由于道德的自由没有仅仅把自由解释为人们直接地享有的东西—即仅仅通过要求自由就享有的东西—因此,它再也不可能仅仅凭着自己对自由的直接要求,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承认人格的直接权利,但它认识到那些权利的特征是不确定的,受此指引,它把它自己的真实自由定位于它坚持那些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它假定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有责任,从而它是自我规定的。因此它明白,真正的自由并不仅仅存在于对人之自由的断言之中—虽然这是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一更确切地,它存在于主动的自规定之中。
310
伦理的意志与道德的意志之间的差别很简单:道德的意志认为,善是它能够自己认识或规定的东西,而伦理的意志则承认,善是它在周围世界中遭遇到的某种现实的东西。因此,伦理的意志重新考察了曾经呈现于抽象权利这个层面的一种理解,道德的意志以为它也具有这种理解,但实际上它却遮蔽了这种理解。这种理解就是:自由与权利善一本身有着确定的特性,是客观的、必然的,明确地超越了一切“主观的意见和任性”。
《黑格尔导论》读后感(三):《黑格尔导论》(1、10章)读书笔记
调和宗教本体(启示)与逻辑本体(哲学)的工作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线之一,前者是信仰的对象,后者是认识的对象。两者也被称为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双城记”。两者分殊明显但都被当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φυσικάμετά)的客观实体。人是“主体”而非实体,人只是“精神”或“上帝”等实体的一个现象,人的主观性的“实践理性”(道德)不过是客观性的“绝对理性”的一种反映形式,根基在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似乎很少上升至本体论的层次,康德可能是一个例外,在柏拉图强调善、美德的同时也不断攀爬至理念本身的形而上学本体高度)。
毕达哥拉斯揭示了不能触摸的数字、三角形及其他几何对象的永恒、不变属性,巴门尼德以后柏拉图也确立起了存在(being)的世界与生成(becoming)的世界的区分,存在的世界的容器里装的是所谓“理式”(Form),如善、好、美、等等。比如,在个体身上的美、善都是暂时性的,不具有永恒、不变的属性,再美的事物也会明日黄花,而只有上升到美本身,这样的追求才会达致永恒的世界。柏拉图宣称两个世界的鸿沟不可抹灭却可以融合,肩负这个任务的就是哲人王。而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本身并不为我们所了解,两个世界无法被统合。
古典哲学将自然的善、目的作为生活的指引,哲学是被善所吸引的生活方式,而在基督教系统里,则能够以宗教本体(上帝)的立法、灵魂的拯救为依据提出更高的善和目的,或者说以超自然和超越来引导自然。托马斯•阿奎那正是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一面向,才把哲学(理性)当作为信仰(启示)提供依据。
黑格尔和柏拉图一样认为关于整体(the whole)的知识是可以达致的,但依靠的不是哲人王而是“时间”,真理是在历史的结构中达到的,最后那个完美的自我规定的自由世界就是“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宣称自己并没有取消上帝,并把自己当作一个虔诚的“路德派”,但像卡尔•巴特这样的神学思想家对此并不买账。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似是在调和启示与哲学,但他降低了上帝的尊贵,不但人分有上帝的形象,上帝也变得在本质上“属人”。对于尼采来说,“上帝死了”是在说“对上帝的信仰不再是值得尊敬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这告诉了我们上帝的本性就是变成人、受难而死。这与“三位一体”的传统之间的差异不可磨灭(霍尔盖特在本书里为黑格尔进行了辩护,认为黑格尔对基督教和思辨哲学的统筹恰恰体现了基督教的核心)。注:笔记只涉及本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
黑格尔不接受无中介的知识(unmediated knowledge),他将“范畴”(形而上学)作为经验的预先框架。“我们遭遇的世界总是通过一个我们无法取消的范畴框架而被经验到的”(p2),康德也是如此,我们感知到这个世界并非是单纯地这个世界的东西“被给予”我们,我们是积极的、有理性的是者。但与康德不同的是,康的认为“我们无权声称,世界自身是根据这些范畴建构起来的……我们无法知道世界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p3),我们施加于世界东西不可能合乎世界本身。但黑格尔认为我们的概念、范畴结构与世界自身的结构是同一的,例如“因果性”作为一个范畴,它确确实实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构成性的”特点,而不是我们“强加”给事物的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康德认为基础性的范畴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固定不变的,而黑格尔引入历史哲学以后,范畴便不是变动不居的。“绝对知识”可以获致,但它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并且永不变动,它只有在一些比较高级的文化中才会被发现,历史的终结时才会达到。“对于康德来说,范畴构成了知识永恒的先验框架,而对黑格尔来说,它们则构成了知识变化着的历史性的前提”(p5)。他认为,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概念预设,文明有其自身的历史特性。
霍尔盖特比较了黑格尔与库恩的观点,两者都认为“我们并不是首先对事物具有直接的经验,然后再对它们做出解释;我们只是首先处于一个特定的概念预设框架之中,才有了对事物的经验”,库恩称我们总是通过所谓“范式”来看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虽然我们所经验的这个世界本身并不会随着新理论的出现而变化,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则依据我们预设的范式而发生了变化”(p7)。重要的区别在于库恩的科学发展进程不存在任何终点,范式是一个无限地展开的发展模式,而黑格尔认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自由,意识到我们自我规定的潜能,越来越意识到自由在世界之中得以实现和达成的途径”,这个自我察觉过程有一个“终点”,那就是这个时刻:“所有人都具有成为自由的、自我规定着的能动者的潜能”(p8)。
黑格尔对历史性的“先行概念”(preconceptions)很敏感,“我们要理解其他的文明,就必须揭示出塑造了它们的那些独特的先行概念”(p8-9);虽然不存在普遍的效准,但仍可以根据“自我规定”的自由程度来辨识出一个文明的基础性信念,这些信念使得我们能够把这个文明历史性地置于与其他文明的关联之中。而黑格尔相信,在一个文化的宗教当中,能够最为清晰地看到一个民族的基础性自我理解,“基督教体现了人的自觉或自我意识的一种更高的、更加深刻的形式”(p14)。由此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高峰。
黑格尔认为,所有的文明在“事实上”都是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无论它们自身是否是“有意识地”这么做(也许并不以创造世界为目的、也没有察觉到这一进程)。但人类的本性便是自我规定者,历史中的“根本性进步”便是“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是自由地自我规定着的,从而,人类在历史中现实地变得越来越自由地自我规定着”(p18),这是一个“使我们成为我们已经是的东西”的过程,创造自己和发现自己是一个融合(self-realization);尽管不存在文明间的共同范畴,但“一个更加自觉的文明可以证明,它对人的‘本性’和潜能有着更深入的理解,随之它也有着更强大的力量”(p19);希腊文化无法容纳“主观自由”,无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批判性的审查之下,所以苏格拉底被处死;而后来的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宪政国家可以容纳个人反思的自由,因而具有历史的优越性。惯常的思维认为“绝对的真理”不能容有“历史”,但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对立,历史与绝对真理融贯起来:“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凭借这个过程而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自我规定着的,因而也是历史性的。人性的绝对真理就是,我们是历史性的,而人性的历史就是认识到我们绝对的、历史性的特征的过程”(p22)。
意识到自我的自我规定性并不是一个平稳的过程;不是所有的历史都能成为“历史”,“只有那些由人的自我意识、由对有意识地阐明的目标的追求所导致的事件序列,才能够真正地被看作是历史的”(p26);霍尔盖特认为黑格尔不是相对主义,因为他认为有些文明要比另一些更先进,有些文明是“最深刻地自觉的”;黑格尔的“绝对”也不是为全知全能的操控者谋划,人对历史的创造并不等同于人对历史的掌控,“人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并不总是像他们所意图的那样”。
但黑格尔的“理念”(Idea)不是一股超验的力量,“理念是内在于世界自身的合理性(rationality):世界自身固有的逻辑”(p36,不同于康德为“超越性”保留空间,黑格尔采取了现象学的进路,真理是现象界的真理,不再存在高于历史现实的东西)。
绝对精神就不是超越性的宇宙真理,“它只是是本身在我们之内、作为我们,开始意识到它自身固有的合理性”(p387);在理性的活动变为我们自己的活动这一自由进程当中,黑格尔认为基督教和思辨哲学达致了合一;宗教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的意识;哲学与宗教信仰之间本身是独立的,但在人身上,只有兼顾两者才能有对真理的确切把握;“在黑格尔看来,‘上帝’这个宗教的语词就是哲学认识到的理性或‘理念’,也就是活跃于世界之中的绝对理性”(p390);“爱实际上是合理性实存的恰当意象……我们在被绝对的东西支撑和保护着,我们只能把这种感受思考为被爱”(p394,在尼采看来是靠不住的东西,黑格尔认为那是被爱,然而这个爱多么冷淡啊,爱都得是合理性的);信仰使得真理更具穿透力,真理进入了我们的内心和想象;由此有一个分岔口:宗教在基督徒哲学家看来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宗教“不能用理性来解释”(non-rational);宗教在非基督教哲学家看来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宗教是理性的对立面;而黑格尔认为宗教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的本质。
“道成肉身”就是绝对理性内在于这个世界;黑格尔因此严格区分基督教和犹太教(三位一体中黑格尔似乎是着重了圣父与圣子的同一这个面向,超越性被取消了);黑格尔的上帝是“生动、在场的上帝”;上帝牺牲了超验的权柄,替之以“自我奉献的爱”;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于“确信我们与上帝根本的同一性”,“我们在他之中看到的上帝不是避免了人的有限性,而是在人的有限性之中把他自己揭示为人的有限性”(p407);信仰承认了“终有一死”的事实,但并没有把死亡当作生命的终点,而是“一扇门”,这并不是强调我们应该期盼死亡;霍尔盖特强调黑格尔与路德的同一,两人都认为“基督徒的意识因而首先是一种变得完整、获得自由的意识——在基督之爱的精神中摆脱了死亡,获得了生命”(p416);“上帝的本性就是变成人,受难致死”(p428),纡尊屈贵这一上帝的行为被当成了上帝的“本性”。
注:历史哲学(该术语由伏尔泰创制)的确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因为它依赖于“历史神学”,时间的引入确立了历史的进程有一个终极意义,而纯历史没法提供,正如洛维特对历史哲学的评述:“关于普遍历史的一个系统性的阐释,使之与一个原则符合:通过这个原则诸历史事件和序列被统合起来,并被导向一个终极意义”;“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宣称不管个体、民族在历史中的行动出自何种私人的目的,理性的狡计仍然会确保它们成为历史目的实现的动力,这当然是“上帝”计划的神意了。
《黑格尔导论》读后感(四):读后感
以历史哲学的意识发展为开头,以基督教与绝对理念的一体两面为终,从无预设的是态逻辑学到意识的现象学发展,外化为具形化的精神(自然),演化出生命,上升到精神,发展出伦理共同体,再到艺术审美去寻找问题的真解决,最后回归内在体验(宗教)绝对精神到此结束。作者绝对是黑格尔的死忠粉,竭尽所能为其辩护,我认为主要的逻辑学和现象学笔墨少了,而自然哲学却占了大头,黑格尔这种理想主义也真是有种独特的魅力,很玄学,给我看的都有点信了,艺术和宗教部分,尤其是宗教,叙述有些琐碎反复,当然读起来是很顺畅的,讲述的虽然琐碎但胜在详细,就是可惜了逻辑学笔墨太少,雨露均沾的必然结果,感觉有些重要的部分反而一笔带过了,但是我是零基础读的这本书,感觉没有太大障碍,很适合初学者进入黑格尔的语境,稍微懂点观念论就能看,尤其是谢林,黑格尔的哲学不怪谢林诟病,某些方面还真是相似,没看太细,只能说大致过一遍吧。
《黑格尔导论》读后感(五):第一章“历史与真理”总结
第一章中包含了黑格尔的思想如下:
原文地址
(1)人类的所有意识都贯穿着思想范畴,范畴是一切经验的中介。
(2)与康德认为范畴永恒不可改变、没有历史不同,黑格尔主张范畴是历史性的。
(3)范畴的历史性表现在思想范畴向着思想的自我规定或自由发展。
(4)不同区域文明、不同时代的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精神或者思想范畴的差异。
(5)特定文明、特定时代的法律、政治制度、艺术形式、宗教信仰等等都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6)不同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身是自我规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自觉地因而自由地自我规定着。
(7)评估不同文明程度的尺度就是判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和理解了它们的自由规定。
(8)真理与历史不可分,真理是历史性的,也即是真理是自我发展的。
(9)世界历史的发展尽管存在诸多偶然性,但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对自我本质的自由的理解的发展(波斯帝国→ 古希腊→ 罗马→ 基督教→ 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
(10)唯有人才有历史,自然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自由的发展历程。
(11)人类历史的书写与现实的历史事件是同时出现的,历史的变化是自我记录、自我解释的活动。
(12)国家作为有着共同目标的共同体提供内容于历史,历史叙述把国家的事件客观化并给予保留。
(13)人的自我理解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14)在历史的顶点,人类完全地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自我创造的存在。
(15)现代社会的意识认识到人的本质是完全自由的、自我规定的存在。
(16)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如贫困、异化、不平等、痛苦等)根本上是由于我们没有完全理解真正的自由概念。
(17)现代社会的哲学任务因此是阐明真正的自由概念和自我规定的概念。
《黑格尔导论》读后感(六):关于sein的翻译问题
随手提取两个例子:
正文p70,霍尔盖特说道:“在我看来,黑格尔逻辑学的这个形而上学、是态学的方面——它既规定了思想的结构也规定了是的结构这个事实——是不能被否定的……”
正文p70:“然而,逻辑学不能仅仅是对思想之本性的一个说明,它还必须是对是本身——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称之为“实存”或“现实”——之本性的一个说明。”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本书里ontology就应该被翻译为本体论或存在论也行,但无论如何不是丁三东先生所想要翻译成的是态学,因为霍尔盖特已经很明显在这里提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联。没有人会认为思维与是是一个对子,只有思维与存在才是一个对子,这一点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也表现得很明显。此处将sein翻译为“是”严重影响了读者对p70-1的讨论的理解。如果此处把所有的“是”都替换为“存在”,则一切都无比清晰明朗。
根本不需要区分得过于严密,因为sein根本上既是“是”又是“存在”,首先接受这一点,并且在译注中表现出来,事先提请缺乏相关前提知识的读者注意,就足够了。至于existence,跟随老邓将其翻译为“实存”已经是一条翻译定式了,所以“存在”与“实存”的差别读者自然也能轻易区分出来。
另外,在黑格尔体系里,对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做出严密的区分是一种反黑格尔的行为。脱离了逻辑学的概念规定则无从谈及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甚至实存。丁三东先生对于存在的理解受现象学影响太深,因此根本上(无论有意无意)误解了观念论语境中对于存在的讨论。
正文p170:“《逻辑学》以下述洞见告终:是最终被证明为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或曰黑格尔所谓的‘理念’。因此黑格尔被证明是一个观念论者,这不是由于他认为对象只实存于心智之中,而是由于他把是本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
把这两句改成:“《逻辑学》以下述洞见告终:存在最终被证明为自我规定着的理性,或曰黑格尔所谓的‘理念’。因此黑格尔被证明是一个观念论者,这不是由于他认为对象只实存于心智之中,而是由于他把存在本身理解为理性的。”就无比清晰了。being在本书大部分涵义中就是“存在”。
此外rational就是“理性的”。“理性主义”或“唯理论”不是什么reasonism或Vernuenftismus,而是Rationalismus=rationalism。rational和rationality单独出现时,建议译为“理性的”与“理性”;当与reason并存时,译为“合乎理性的”与“理性性”。总之不要译成“合理”,因为中文里的“合理”有非常明确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与rational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