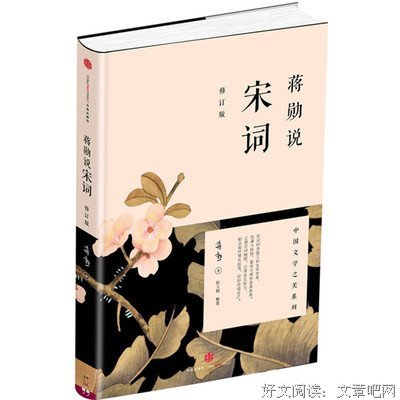《蒋勋说宋词(修订版)》是一本由蒋勋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一):话词(6)——浅谈夜晚的美学意义
夜晚或入夜时分,大概是词人最重要的创作时段。在这段时间,人可以由社会角色转变为个人角色,退回到本身。没有了周遭外界的干扰,人们开始找寻自我,因而夜晚美学的意义多半在于自省。
月和梦大概是夜晚创作时最常出现的意象。比如,“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李煜,《玉楼春》),宴会结束之时,吩咐旁人不要点灯,而是踏着美丽的月光回宫。这一点美丽的月光,都不能浪费,李后主对美的享受近乎偏执,如此追求,亡国的宿命大概是注定的。再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李煜,《虞美人》),听到了东风,看到了月明,这是李后主失眠后的一种状态。缘何失眠?从贵为君主,到沦为阶下囚,生命的落差,让他不安,更让他难以入睡,夜晚时分这种怀念着远方故国的心情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乌夜啼》),睡不着,便独自凭栏远眺,似乎在跟月亮说着悄悄话。再比如,“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李煜,《捣练子令》),难以入睡时,李后主便数着窗外捣衣的声音度过漫长的黑夜。像这样的在夜晚中创作的诗句,李煜还有很多,换句话说,李后主大概算得上是一位失眠的重度患者,但失眠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当时的生命状态,由亡国前后的诗句便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词人偏向于夜晚创作诗歌。比如,“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冯延巳,《鹊踏枝》),这是很容易入画的场景。风吹袖起时,再看月亮,感觉又会不一样,似是一种饱满的生命状态,但同时又带着一丝孤独空对明月。似乎矛盾的两种状态在此时共存,,这或许不难理解。当你感受到生命中最大的喜悦时,或许也怀着最大的感伤,这种双重感情估计也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体悟到。后半句的人归后,虽提到了人,但词人其实并没有看到人,只看到人归后的一种自然的状态。不从人的角度去看景,是宋词别于唐诗的特点,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促使词人以一片叶、一瓣花的姿态去融入自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再如,“明月高楼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范仲淹的思想之情,借着一壶酒,被明月照的一干二净。再如,“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和“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晏几道,《蝶恋花》),晏殊父子二人的生命体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父子二人失眠时不像其他的词人四处游走,凭栏远望,而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父亲将离恨之苦寄托在明月之上,透过窗户照进了心底;儿子却将注意力放在了床旁的屏风上,心之所想似乎映射到了屏风之上。
如果说月亮是失眠者的伙伴,那么梦就是伙伴送给失眠者的礼物。比如,“路遥归梦难成”(李煜,《清平乐》),被俘后对故国日思夜想,但这却是一个绝望的梦,李后主彼时那种憔悴、哀怨已经到了顶点,以至于在梦里都觉得归期难料。再如,“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蒋勋曾说中国文学史上宗教感和哲学感最强的一句话莫过于此。它适用于任何人的一种生命形式的告白,踟蹰于那些最深的感情,包括对父母的依恋、对爱人的眷恋,好似是“一晌贪欢”,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生命的终极归宿。也只有在夜晚时分,在梦里,心境才能完全沉淀下来,不带一丝杂念去体味这样的谶语。到最后,李后主对故国的思念变成了对人生的终极思考。有人在梦中思考,有人则在梦中去经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比如,“夜来幽梦忽还乡 ”(苏轼,《江城子》),东坡对亡妻的思念也只有通过梦境获取一丝慰藉了。再比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稼轩做梦都想再战沙场,收复山河,可惜这也只是一场梦。一边是抵御外辱的决绝,另一边则是壮志未酬的遗憾,辛弃疾只能在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除了凭栏赏月,或卧床望月,词人的失眠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遥夜亭皋闲信步”(李煜,《蝶恋花》),李后主这次失眠后却走在了河边,或许这样,让他觉得离大自然更亲近些。再比如,“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此种场景,对于我们或许再熟悉不过了。失眠后的最直接表现便是辗转反侧,因为被子上绣着红花,所以被词人描绘为“被翻红浪”,形象至极。
蜡烛是夜晚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也是词人常用的一类意象。比如,“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晏殊,《撼庭秋》)和“红烛自怜无好意,夜寒空替人垂泪”(晏几道,《蝶恋花》),父子俩在蜡烛面前又一次地心有灵犀。所谓心长焰短,即烛芯还很长,只是蜡烛快要烧完了,而蜡烛所滴下的蜡油如同垂泪一般。张爱玲说这是一种生命状态,空有一腔热情,却没有燃烧的机会了,因为生命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种无奈、那般不甘,通过“心长焰短”被变现的淋漓尽致。而晏几道则通过红烛表达了心底的那份孤独空寂之感。
以上都是在讲入夜之后的情境,而从白到黑的入夜阶段,也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词人也经常以此作为创作契机,通常表达的是惋惜、珍惜之感。比如,“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祁玉,《玉楼春》),词人和夕阳之间似乎展开了一场对话,向天边的晚霞问道:可不可以在花间多停留一下?词人想把在花间的美好体验再延续一下。可是,夕阳就是要入夜的落日了,留不住的。“花间”和“晚照”让词人产生了一种珍惜的深情,那就是在入夜以前,至少还能够和繁华在一起,虽然美好势必要结束。此种深情最终也变成对生命的祝福,生命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从容。再比如,“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又是夕阳西下,想到彼时的王谢堂前燕,却看到此时寻常百姓家,作者将对国家兴衰的感叹在即将入夜时表达了出来。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二):蒋勋说宋词-话词(4)——浅谈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之焚香
唐诗和宋词之间的最大的差异,除了表达形式之外,应该算是意象的转变了。唐诗多集中在比较大的意象上,在山水之间,在天地之间;而到了宋词,居家之日常逐渐变成了词人笔下的意象。这样的差异源自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唐朝疆土辽阔,因而思想也是向外发散、扩大的;而对于两宋来说,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大部分人的思想是向内收敛的,这个时候人们便会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周遭的寻常细微之物上,常常是一种生活化的、细节化的生命体验。本篇将主要讨论一下宋代文人居家日常之焚香。
香文化发展到宋代,已经从庙堂之上延伸到了寻常百姓家。香炉,作为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常常成为宋词人笔下的意象。一方面,这是调养心志的把玩之物;另一方面,香炉内的熏香也有养生祛病、供神祭祀之用。比如,“炉香静逐游丝转”(晏殊,《踏莎行》),炉内所燃的香末,形成了一缕青烟,如游丝一般,绕着香炉在转。这样的景象是绝对要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细细品味的。如果是山雨欲来,如果是心潮澎湃,想必都观察不到如此细微的景致。唐诗中便少有这样的描绘,大多时候都是在描绘更大的意象。而对于宋代词人来说,因为政治上的安逸和经济上的繁荣,使得他们有机会去观察那些眼前的东西。炉香绕着香炉在转,这可能是一个再直白不过的描述了,甚至没有任何的意义。可是难道生命的每时每刻都一定要有重大的意义吗?未必,有些安宁的片刻谁都不属于,是一种放空的状态。香炉是个微不足道的物件,但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就是由这些微不足道构成的吗?再如,“燎沉香,消溽暑”(周邦彦,《苏幕遮》),这其实就是在描绘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动作——焚香,如同沏一壶茶、浇一盆花一样普通、简单。燎,意为细细的焚烧。为什么焚香?可能夏天的暑热让词人有些不适,于是便燎一炉香,以达到驱除蚊蝇、提神醒脑之功效。由此可以看出,焚香在这一时期已成为词人很重要的生活经验,是居家日常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再如,“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李清照,《醉花阴》),李清照同时使用了嗅觉和视觉体验。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铜香炉里放了一种称为瑞脑的香料,慢慢燎起来,铜香炉上所刻画的金兽,便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作者似乎是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可是又不知何处安放?想来想去,只好通过焚香来表达出来。而到了“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作者则将嗅觉、视觉、触觉三种感觉结合了起来。金猊,即香炉所刻画出的神兽,形貌类似狮子。手摸了一下香炉,已经变冷了,大概是因为炉内的香末燃尽了。一“香“一“冷”之间,词人的哀愁又更深了一步。正是借助于对香炉感官化的描述,作者可以将当下的心境直接表露了出来。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三):《蒋勋说宋词》书中宋词摘录
李煜
007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011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012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18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021 蝶恋花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023 长相思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025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四):宋词之美
一直很喜欢词。看到词本身没有细读,都会觉得每个字都好美,逼格好高的样子,如果细细读来符合音律,又会读第二次,再次每个字每个词的看过来,看用了哪些字词,让人耳目一新。
蒋勋先生的这本书,对我等外行来说,很适合,跟着他一起慢慢评析一首词,当然他带入许多自己的感受在里面,但有些典故,字词如果没有专业的人来点出来,单凭自己还是很难消化的。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就有用种他是导游,而我们是游客的感觉,一步一景,一首一首的讲过来,仿佛在眼前画出了词的意象,也够了出了作者的形象。同时在讲解中讲人生的大开大阖,也讲生活中细微末节。喜欢苏轼的圆肚子和他的豁达性情,虽然常常在悟道但是总是破相,完了又哈哈大笑,善于化解自己的忧愁。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独立小桥风满袖
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五):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
读好书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在读书这一刻让自己昏昏沉沉的大脑突然有了那种渴望已久的神清目明的清爽之感;就是让自己焦躁不安的心情突然有了那种落地为安的踏实平和之感;就是借了、读了但还不甘心,非要下单买了纸质书收归囊下占为己有的满足之感!
零星地读过蒋勋的《孤独六讲》、《吴哥之美》,而对谈论中国文学之美的这套书始终未敢触及,唯恐阳春白雪,高不可及。趁着kindle Unlimited畅借之际,借了几本往日里既想读但又有些犹豫不愿下单的书,其中之一就是《蒋勋说宋词》。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喜欢上特定的某种文学形式,因为在自己的感觉里这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最契合当下的自我状态和心境,而喜欢唐诗、宋词估计是最多的。但喜欢的时候或许太过年轻,或许年少,能够背诵,却未必深刻理解和领悟。依稀记得自己捧着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狂背的那一个个清晨,那一轮轮旭日,还有那个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
蒋勋先生以他平淡朴实的言语让人跟随着重新走进这些诗词,他以唐诗宋词为载体,着墨于诗词之美的分析,却又力透纸背,强调文学与历史环境、时代背景的息息相关,与人性的息息相关。唐诗的大开大合与宋词的小桥流水人家是诗与词的差别,也是唐朝与宋朝的差别;李白与杜甫必是唐朝的诗仙与诗圣,苏轼与欧阳修只能是宋朝的才子,他们都无法穿越时代。蒋勋先生把诗词的背景、时代、意境、意向表征解释的如此细微通透,读着,有种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只觉得能捕捉大诗人、词人们那一刻的心境了。中国文学的美,在这一刻,淋漓尽致,但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词之美就在于享受生活中的平凡与平静,超越喜悦与悲伤是其追求的境界。” 这也是人生的境界吧。
春天到了,读一阙苏轼的《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真美!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六):话词(5)——浅谈空间的美学意义
前面几篇话词中,基本上都在讨论单个意象,或2个意象的搭配,那么当多个意象组合在一起呢?这就形成了一定的空间,词人通过营造这种空间感来表达情感。空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生活空间,自然空间。
前面也提到过,从唐到宋,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文人眼里的意象逐渐从比较大的山水、天地转变成周遭的日常之物。我们会发现,日常居家之中所形成的空间常常出现在词人笔下。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 ”(欧阳修,《蝶恋花》),叠字的使用直接点出了家居的空间感,通过描述,我们可以猜测词人所在的是一个大户人家,多个院落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古代的宅院根据纵向的扩展可分为一进、二进、三进、四进等。一进,一般由四面或三面房子围成的院落,房间又分为正房、耳房、厢房等,不同的房屋类型有不同的功用。二进,在一进基础上沿纵向扩展,即在东西厢房的南侧加盖一面墙,可将原来的院落分为内、外两重。三进,在二进的基础上,在正房北侧加盖一排后罩房,可穿过正房两侧的耳房到达后院的后罩房。一般,三进来说,已经可以算是比较大的宅居了。当然,房屋的主人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喜好构建个性化的大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进、到二进、再到三进,是依靠隔断划分出来的。隔断最常见的形式便是墙。比如“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苏轼,《蝶恋花》 ),像东坡这样的高手,即便是在白描时,也会用很高级的手法把它表达出来。这种高明之处就在于空间感,一道墙分出了两种空间,一边是道,一边是秋千,道上有行人,便是东坡自己,秋千上有个姑娘,正在欢笑。正因为这种空间感,东坡才会循着声隔着墙去看另一侧的情况,这才会有后来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唐突。
但是,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墙这种隔断形式其实出现的比较少,词人笔下更多的是纱、恋、幕、屏风这种更加具有美学意义的形式,似透非透的感觉,隔断之中有连接,连接之处又形成隔断。比如,“翠叶藏莺,珠帘隔燕 ”(晏殊,《踏莎行》),一藏一隔之间点出了珠帘所形成的那种空间感,将生活起居的空间与草长莺飞的自然空间划分了出来,但似乎划分地又不是那么明显。再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醉花阴》) ,只要大自然稍加外力,便将生活与自然这种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人在屋内,便也感到了几分凉意,而这种凉意则直达心底。再如,“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 ”(晏殊,《撼庭秋》),此时划分生活与自然的界限由帘变成了纱,透过纱赏月,更凸显出了一种朦胧之感。再比如,“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晏殊,《蝶恋花》),此时隔断的形式又变成了罗幕,这是这种似透非透的感觉,这便使词人形成了一层心幕,想看清外面的世界,却又无可奈何。相比于其他几种隔断,屏风,我个人认为是最具美学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形式。更准确地说,它已经从日常居家之物上升为一类工艺美术作品。比如,“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晏几道,《蝶恋花》),看似在描绘吴山的景色,实则是在描绘屏风的画作,真假之间也反映了词人酒醉后的一种状态。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宋朝的家居布局。由窗到床,屋内的小空间通过屏风又形成了一种层次感。再比如,“淡烟流水画屏幽 ”(秦观,《浣溪沙》),所谓的淡烟、流水,并非实景,而是屏风上的虚境。词人看似在外赏景,实则在屋赏画。恰恰是屏风这个隔断,让词人写出了一种“幽”的感觉,躲在屋里可能有一点烦闷,有一点无聊的感觉,那是一种沉湎的生命状态。
其实,宋词中也不乏有大意象所组成的空间,一般是山、水、天的组合。看到这些词,脑海里瞬间就可以浮现出那种空阔的画面。比如,“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李煜,《长相思》),一和二的使用,凸显出了空间渐变的层次感,从水望到山,再望到天,李后主的那种思念浓得形成了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下文的“相思枫叶丹”,那种思念把叶子都染红了。再如,“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范仲淹,《苏幕遮》),水连接着山,山又连接着天。在这种空间中,词人以斜阳作为参照物,斜阳照着山,可是芳草却又在斜阳之外,为什么呢?因为芳草无情,那是一种空间上的不可及所描绘出来的感伤。再比如,“提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欧阳修,《浣溪沙》),这是一幅更加细腻的空间景致。天下堤,堤边水,水上船,船中人,如此多的层次表达了词人水上春游的一种喜气。
欣赏这些词人所描绘出来的空间美学,就好像卞之琳在《断章》中所说的那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王国维也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话放到空间美学的意义中同样适用,内心有怎样的格局,笔下就会写出怎样的空间。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七):蒋勋就是台湾的余秋雨
作为读书笔记的开篇,关于这本书的讲述会非常少而简单,我会多费点笔墨在阅读这件事情上。
(我给自己新定了个任务——每周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
读书,一直是我的主要爱好之一。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儿子,小时候没有像样的书看。到了小学,偶尔能借到高年级小伙伴的课外书,在夏日午后,读一本已经翻烂的书,那种幸福,一念及还仿佛昨天。到初中,有点零花钱可以买书了,但仍很有限。
当我到了高中,第一次走进图书馆,那感觉真是神奇极了。如果今天给北韩民众接入互联网,估计他们可以体会我当时的感受。
是的,我真正的阅读从高中才开始。那时候才开始接触王国维、胡适、鲁迅、钱钟书、老舍、茅盾、三毛、梁实秋、莫言、余华、石康、沈从文、刘震云、顾城、海子、北岛、食指。。。就像我现在噼里啪啦打出这些名字一样,高一那年,这些人就是这样噼里啪啦地闯进了我的世界。中间也涉猎了弗洛伊德、莎士比亚、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等老外。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上高中还要好的了。
因为我是住校生,所以我的阅读史是与我的自由史一起开始的。
我所在的高中非常宽松自由,每天只有上午有课,下午和晚上都是自习课。高中的三年我几乎下午都在图书馆,晚上一般时间都在阅览室。
我甚至还成了图书馆的兼职管理员,帮助新书上架,帮助登记其他同学的借阅,重点是,我可以进到里面一个不开放的空间,读到很多不开放的资料和书籍。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其中一个矮矮胖胖可爱至极的年轻女馆员,我很少可以那么清晰的记得一张快二十年不见的脸。
记得有一天晚上,馆员们都走了,她们锁上门,但忘记了里面还有我。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走的。于是,我被锁了一晚,最要命的是,没有地方上厕所。
事实上,我无法确认这段记忆的真实性。或许是我一个人躲在角落看书时常常担忧发生这样的事情,慢慢虚构成了一个回忆。
高中的阅读体验一直影响着我,之后再也没有那么疯狂的阅读时光,但是它就像初恋一样,指引着你对恋爱这件事情的信仰。
到了大学,因为自由的身体突然获得了自由的意识,时间开始有了新的分配去向,比如兼职、比如恋爱、比如运动、比如喝酒。。。阅读依旧是独处时最好的朋友,只是独处的时间有限。
工作的头几年,阅读的时间进一步被压缩。后来自己创业了,阅读量才大致回到大学的水平,现在也差不多。
决定这次阅读计划的时候,我正在同时阅读两本书,另外还在听一本书(听书这个习惯,我今年才慢慢接受、适应),其中一本就是《蒋勋谈宋词》。
而就在前几天,鄙人老来轻狂,喝多了跟夜场的保安干了起来,结果被打的嘴唇破裂,缝了十几针。今天去复诊,出门时料想医院排队必定费时无聊,便带上了已经看了小半的《蒋勋说宋词》。结果等号的时间远远超过我的预估,剩下的一大半,在医院嘈杂的过道看完了。
我对陪我去医院的朋友说,别人看我这个捧着书如饥似渴的装逼样,一定想不到这孙子的嘴唇是跟夜场保安无故斗殴被打破的。
这很有意思。喜欢读书和文质彬彬没必然关系。你去看看高晓松。
有的书是读不快的,但是蒋老师的书是可以读得快的,就像余秋雨的书。这类书的特点就是不求甚解,所以读起来很轻便。我觉得这本书作为了解宋词启蒙书还是不错的。
这应该是一本由录音讲稿编辑成的书,文字很松散,很口语,不过也恰如其名,说宋词嘛。
唐诗也好,宋词也好,我们认识它们、认识它们作者的经验,跟我们认识其他的文学类型和作者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认识王国维是高中的事,因为我那个时候才看的《人间词话》。大部分的阅读是一种严肃的介入。但是唐诗宋词不一样,它们会见缝插针地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时刻闯进来。可能三岁,可能十三岁,可能三十岁。
这也是我觉得读这本书还算有趣的地方,它里面从五代到北宋到南宋依次列出的那些经典,每一首都勾起你第一次或者其中一次遇见它、阅读它的场景、心境。这跟我们偶尔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的感受是一样的。伴随着作者的碎碎念,你进入词的意境,这个意境和你的“想当年”混杂在一起,词句本身又有了新的活力。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至于书里涉及的一些关于文学与美学的思考,可惜要么浅显,要么不满意于作者的洞见。总之,鲜有启发之处。
草草结尾:一本轻松的读物,一个感性有亲和力的作者。如果你本身喜欢宋词,可以选择这本书来重温那些经典。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八):文化美学的王朝
唐诗为何会变成宋词?
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变得高不可攀,虽然意境越来越高,同时也远离了民间。盛极而衰。
宋词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而将流行歌曲由“伶工之词”提高意境到“士大夫之词”的重要人物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前半生醉生梦死,后半生亡国之痛,命运的错置却成就了宋词美学上的极品。
北宋的著名艺术皇帝宋徽宗,对文化的热爱在历史上的皇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便是一个明证。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由此今天的我们才能有幸看到历史上的真迹宝藏。
文化上没有李后主或许就没有宋朝的词;
没有宋徽宗或许就没有南宋之后那么高的绘画成就。
2位皇帝在文化上的贡献是惊人的。
苏轼、柳永、欧阳修、范仲淹、晏殊,
生产了众多大家。
《水调歌头》、《临江仙》、《江城子》、《雨霖铃》、《蝶恋花》、《浣溪沙》、《醉翁亭记》,
贡献了绝世名篇。
珍藏于台北故宫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书法的随意,写错了就点一点,改一改,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掩盖它。
书法的真性情。
不同于唐朝大山一样的豪迈,
多了如水一样的柔美和温和。
雄壮是一种美,微小也是一种美。
宋朝,包容之美,深情于万事万物。
宋朝为什么会是这样文化美学惊艳的王朝?是否有以下因素:
001繁华带来的安定
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必然绕不过去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汴梁。北宋的汴梁不仅繁华,更是具备了近代商业城市的基本规模:最早把住宅区、商业区、游乐区分开的城市。政治安定,贸易频繁,经济繁荣,人心安定。
002 政治上没有负担
宋朝有“太祖誓碑”,继位的皇帝必须遵守,其中一点就是“不杀士大夫”,皇帝再怎么生气,可以把大臣降职、流放,但不能杀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北宋词的从容,北宋知识分子的坦荡情怀,所以才有了欧阳修、范仲淹这些在官场中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省长或者边防司令的身份,同时还能够写出这么优美的词。
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土壤在宋朝都齐备了。
蒋勋带我重新认识了宋王朝。
这里不仅有品味极高的皇帝:宋徽宗,还有开创了词类发展的苏轼大家。
这里是一种对生活豁达的慢体验。
这里更是一种人生自我思索的新高度。
喜欢这个王朝。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九):话词(1)——浅谈花的泛型美学意义
最近在看《蒋勋说宋词》和《人间词话》,突然冒出了很多想法,遂计划写个系列出来,浅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初中语文课本开始,就已经在考察我们对宋词的理解,但那时我们的理解只是局限在其文学意义上面,更直白一点说,是局限在脸谱化的文学意义层面。比如,我们看李煜的词,脑海中的第一印象便是南唐后主,即便他的词再美,老师也会补充强调一下他的玩物丧志、衰败颓废之感;比如,看柳永的词,总有种异类的感觉,只能另眼相看,为何不能将他与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正统一视同仁?在学校里,老师最爱强调的就是规矩,所以大概不能忍受柳七的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比如,我们看李清照的词,特别是南宋以后,为何表达的多为闺愁、幽怨?如果了解宋室南迁这段历史的国仇,了解她与赵明诚这对知己夫妻的患难与共,并将这两种生命体验结合起来,我们大概便很容易接受她的这种愁,这种怨;再比如,看周邦彦的词,总感觉读起来不是那么流畅,可却又说不出个原由,便以为他的水平一般般,但如果了解他对音乐的追求,或许我们便会增加一份敬畏,如果放在现在,或许他应该算是方文山、林夕那样的词作家,专门为音乐而生的词作家;但是,在学校里,宋词赏析可能只是应试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读史,也不需要去了解词人的个人生命体验,更不需要去研究音律,只要记住老师教的那些脸谱,我们也可以答对那些试题。但是若脱离了文化传统、脱离了时代背景、脱离了个人生命体验,宋词便大失光色。
如果把宋词比喻成一轮明月,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初一的月亮,而蒋勋则站在美学的角度为我们呈现出了十五的月亮。
如果对宋词中出现的所有意象进行词频统计,“花”这一泛型意象,估计可以排到TOP 5。所谓泛型,即不特定指代花的品种,就是泛指花,对世间千千万万的花的抽象。央视有个《诗词大会》栏目,出题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套路就是张冠李戴,即A诗的某一句置于B诗当中,或是将A词和B词混在一起,以此来考察选手的对诗词的熟知程度。从结果来看,大部分人都会落入张冠李戴的陷阱中,泛型意象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此诗与彼诗的意象可能采用了相同、类似的泛型,而这类意象或是这类意象所表达的意境其实大多是相通的,因而答题者觉得选项两可,只能凭感觉择其一了。
花,这一泛型意象是载体,可以将人类内心不可见的情感具象出来。所以无论是探讨花的文学意义,还是花的美学意义,个人认为其实都是在分析人的情感。通常,我们会将人的情感划分为喜怒哀乐,但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如果我们的内心只是由这四个象限构成的平面,那我们的世界岂不是太单调乏味了吗?
人是立体的,因而情感也是多维的。花的种类千千万万,因而所能承载的情感也有千千万万。喜怒哀乐,可以作为父类情感体验,由他们会衍生出很多复杂的子类情感。比如“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表达了词人对于当下自然情景的喜爱之情,也突出了生命的活力和律动。比如“白发戴花君莫笑”(欧阳修,《浣溪沙》),欧阳修在步入中年之后,用一朵花插在头发上,还跟同行好友说不要嘲笑我疯癫,这反映出了作者对生活的一种情趣,总之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就对了。再比如,“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柳永,《鹤冲天》),明明应该是落榜后的失落,作者却不以为然,而是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和欢乐。以上都是在讲喜和乐的,可是细细体味,还是有很多差异的,这个差异是与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命体验密不可分的。
其实,于宋词来说,我最想谈的是哀这种心情,词里虽然写的都是花,但此花非彼花,那是将宋朝的国势和个体经历相结合的最多元化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条件下,哀可以有很多种。如果一个人经历了从繁华到幻灭的过程,会感觉到一种哀,那是一种极度失落的感情。从“临风谁更飘香屑”(李煜,《玉楼春》)到“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虞美人》),虽然香屑、春花都是花,但却截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南唐后主在亡国前后所经历的从繁华到幻灭的生命体验,但即便是幽禁他乡,作为一国之君他所哀叹的也仅仅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与莺歌燕舞的宫娥。从“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李煜,《相见欢》) ,到“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再到“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浪淘沙》) 。一路漂泊来,最终失去自由, 李后主的这种哀以花作为载体,情感不断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种感性的层次感。但是,他通过不断的追忆极力想让时间定格下来,他抗拒时间,因为时间只会给他带来过多的感伤。最终,感伤演化为一种终极的生命体验,对命运的发问,我到底会去往何方?李后主留下了这最后的谶语。对于这样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多情男子,可能没办法苛责他太多,甚至有些可怜。他在命运错置中所表达出的哀的生命体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于我来说,总感觉李煜的这种有些单调,哀的这种感觉一直在加深,一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说李煜的哀是对于失去物质追求的哀,那么李清照的哀就是对于人的哀。是对逝者的悲伤,也是对逝者的思念。如果了解他和赵明诚这对知己夫妻的故事,便能理解这份哀。这种哀伤与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截然不同。比如“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李清照,《点绛唇 》),这是女性视角中的花,深闺之中那一份浓浓的思念之情,犹如熬不化的糖浆,久久无法消散。
李清照,作为历史当中一位独特的女词人,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
其实,以上都只是哀的一个侧面,它应该还有另一个侧面。
花开花谢,皆念恩泽。既然从繁华到幻灭这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我们就与他们安静的共存,既不必刻意逃避,也不必抱憾终身,珍惜一点就好,宽容一点就好,心底留一点温存就好。比如,“百草千花寒食路”(冯延巳,《鹊踏枝》),一边是花,一边是寒食节,对比之间道出了从繁华到幻灭的客观规律。 再如,“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晚照所代表的夕阳本来是感伤的,因为是要入夜的落日,但与花间的结合又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一种在美好结束前的珍惜之情,在失去后,这种珍惜也化为对生命的祝福。这其实不是在讲结束,而是说要在结束前不负自己,不负他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浣溪沙 》),花落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但与此同时又看到新的希望,花的逝去与燕的重逢之间揭示了两种并存的生命状态。心底有哀伤,也有温存,两者不冲突,不对立,都是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今年花盛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红,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 》),更是直接点出了对于这两种并存生命状态的豁达,你可以有不同的生命体验,也不必执念于原来的生命经验。再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词人与花展开了一场饱含深情的对话。花开终究是要花谢的,大自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即便了解这样的生命本质后,词人还要以泪眼想问,此种深情,或许也是让我觉得宋代知识分子可爱、迷人的地方。
对于哀来说,在黑与白之间,还有一种灰色地带,这大概就是蒋勋所说的“颓废”之感。当然,当下的颓废并非彼时的颓废,因此在这里打了引号,这个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某种独特的烙印。从历史进程来看,唐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南宋,这是一个由外向内收缩的过程,由向外征服到向内自省。这可能是在经历过巨大繁华之后必然的心理变化。从繁华到幻灭,我们开始从享受繁华到思考繁华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又何在。比如“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冯延巳,《鹊踏枝》),就属于这类情感,没有大喜大悲,有的只是说不清的无助、道不明的倾诉。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矫情、无病呻吟,但不管你接不接受,这都是多元的词美学的一部分。只是我们没有机会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罢了。
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宋词亦如是。就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晏殊,《临江仙 》),几乎是纯粹的意象描写,至于意境如何就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境如何。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世界可能就是什么样。
《蒋勋说宋词(修订版)》读后感(十):内容推荐
本书系在《蒋勋说宋词》(2012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蒋勋先生按照五代、北宋、南宋的时间脉络,将李煜、冯延巳、范仲淹、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重要词人的佳作一一道来。
在宋词当中,既有简练、淡雅、不夸张的情绪”,也不乏豪放、浓烈与激扬。美从无定规,却皆可成为个人生命的色彩。这是宋词带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慰藉。
阅读宋词,就像在阅读生命本身,饱满与孤独、喜悦与感伤各具其美。记得花间晚照,记得金戈铁马,豁达面对得失起落,好好珍惜自己。
蒋勋先生潜心于艺术与文化之美,“出之于小说、散文、艺术史、论述、绘画,苦心孤诣,重构民族美学与历史记忆,启蒙俗民生活中的感官审美享乐,献身为美的传道者,谦卑明亮,气象恢宏,给了我们欢喜感动与荣耀自豪”。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曾这样描述这位“美的布道者”——“(蒋勋)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唤醒,让我们看见精灿灼人的明眸。善于把沉哑喑灭的美唤醒,让我们听到恍如莺啼翠柳的华丽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