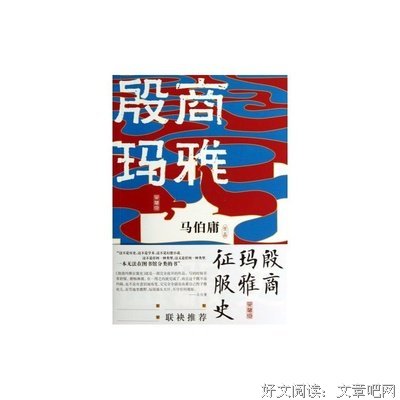
《殷商玛雅征服史》是一本由马伯庸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2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一):《殷商玛雅征服史》西班牙文版序言
《殷商玛雅征服史》西班牙文版序言
墨西哥国立大学考古系教授
胡安·贾舍·维托尔
译者:新垣平
2013年9月31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皮吉加潘镇(Pijijiapan)的警察破获了一起黑帮贩毒案,在郊外的荒地深处挖出了大约五公斤的海洛因。同时,他们也在毒品下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些龟甲和兽骨的碎片,上面有一些古怪的刻画符号。警察们认为这可能和黑帮的秘密交易有关,将这些物证带回去研究了几周。当他们最终发现这些奇怪的刻画碎片与贩毒案毫无关系后,就失去了兴趣,将它们当成垃圾丢弃。大约一周后,几名警官在中餐馆就餐时说起此事,引起了华人老板的注意,他在电脑上打开一些中国河南所发现的甲骨图片,问他们那些东西是否与之类似。警察们感到震惊,在他们面前的图片和丢弃掉的那些废物如出一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在墨西哥会发现本应属于古中国的文物。警官们天才地推断:这是一起文物走私案。但当他们想要找回那些甲骨时,已经为时过晚。这些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的文物已经被在垃圾焚化厂里变成了一堆灰烬。
幸运的是,对其中一部分甲骨,警方拍下了照片。总共有三百多片甲骨的内容得到了保存。经过墨西哥、美国和中国专家的鉴定,发现真相远比人们最初的设想更不可思议,这些甲骨文大概并非贩自遥远的中国,而是美洲本地的产物。事实上,它们证实了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和美洲文明的一次隐匿接触:中国商代的船队曾经造访过墨西哥的海岸。
尽管在学术界仍然有相当的争议,但当这一爆炸性新闻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时,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殷商人曾经到达过美洲的理论,是法国汉学家Joseph de Guignes在出版于1761年的《中国人航海至美洲海岸及亚洲东部若干民族考》(Recherches sur les Navigations des Chinois du Cote de l'Amerique,et sur quelques Peuples situ é s a l'extremite orientale de l''asie)中提出的,此后虽然有一些学者零星地支持这一观点,但却长期被“欧洲中心论”所统治的主流史学界所排斥。人们无法忍受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二十五个世纪,来自远东的船队已经停靠在亚美利加的海岸。
根据董作宾、Mike Xu、Betty Meggers等学者的研究,中国民间学者和作家马伯庸(Mark Bujold)在本世纪初的纪实文学《殷商玛雅征服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aya por la Yinshanga)中重新探讨和推演了这一学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在恰帕斯州的伟大发现后,该书由于其惊人预见性获得了我国的兴趣。不过我国能够流利阅读中文的印第安学者还很少,因此译为西班牙文出版是很必要的。
《殷商玛雅征服史》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尽管充满了对于古代历史的洞察,但毕竟是基于前人研究的一部半幻想性质的纪实文学,从史实的角度来说有若干不精确之处。在今天,我们从被破译的甲骨文,以及在此后几年当地的考古发掘中已经获得了远为丰富的材料,可以修正和补充马伯庸的观点。下面,我将简述近年来中国和美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概括,以便使读者了解殷商人东渡的真实历史背景。
在公元前17至11世纪,一个被称为商或者殷的政权统治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统治者崇信鬼神,他们将占卜的内容用一种象形文字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然后加以灼烧,以裂纹的形态来判断吉凶。这些最早的文字资料,即甲骨文,成为我们了解殷商文化的最主要文字依据。
在若干世纪的兴盛后,在殷商的最后一个国王帝辛统治时期,他试图将王朝的统治扩展到祖先所未及之地,向长江和淮河流域的野蛮部落开展军事行动。甲骨文的资料显示,帝辛将大部分兵力调往东部,投入对“淮夷”的战争中。但帝辛并未察觉,其真正的威胁来自后方的周国。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国的统治者、关中平原的“西方伯爵”姬发联络了一部分诸侯,组织了一支军队渡过黄河,很快抵达殷商的都城朝歌。由于大批军队仍然滞留在东南地带,帝辛不得不将奴隶武装起来上阵,结果是悲剧性的。在朝歌城外的放牧草原,殷商的临时武装一触即溃,周军涌入都城。听到失败的消息,帝辛在他的行宫里自焚身亡,死后他的尸体被姬发无情地蹂躏,头颅被悬挂示众。这一延续了六个世纪的伟大王朝就此灭亡。
然而殷商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着,在河南东部,今天的永城地区,商朝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攸国。这里是对淮夷的战争的桥头堡,其国君喜侯爵是商的王室后裔,也是帝辛的重要助手。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资料显示,当周人发动奇袭时,他正是在淮河前线的商朝军队指挥官。在朝歌沦陷后,喜侯爵和他大约十万人的军队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母国已经被消灭,被视为半蛮族的周人正在潮水般涌入河南平原,另一方面,淮河流域的夷人仍然对他们抱有深切的敌意。丧失了自己的大本营,这一支孤立军队成为了被敌人包围的一座孤岛,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由于史料的匮乏,要精确地复原在1046年之后几年中的东亚政局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周国——现在已经是新生的周王朝了——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直到渤海和黄海,商朝的将领飞廉和恶来在山东的海边被杀死,攸国自身的土地当然也不免覆亡。不过帝辛之子武庚仍然被允许统治商朝的遗民,因此喜侯爵及其尚存的军队此后或许也重返武庚的麾下。
在姬发死后,他的弟弟姬旦以摄政的名义掌握了实权。这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分裂。在喜侯爵的怂恿下,武庚联同姬旦的兄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发起了反叛战争,企图复辟殷商。但却被周朝无情地击败。这次惨败后,喜侯爵知道不可能再和周人和解,于是带领残部逃向长江下游,但在那里也有周人的分支吴国加以阻击。喜侯爵可能听说帝辛的叔父箕子不久前率领其部属远征朝鲜半岛,建立了殷人的新政权,他的部队大概急切地想和箕子会合,但是要越过已经被周人控制的华北地区是十分困难的,那里已经有周王朝的一系列封国。
这一绝境可能促成了喜侯爵选择海路,即从东海出发,越过黄海,到达朝鲜和辽东地区。作为沿海的东夷文化圈的一部分,商人对于舟楫制造技术十分熟谙,在甲骨文中有许多舟船的记载。因此在海边建造一支平底木板船的船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在当时,这一技术仍然是比较原始的。由于缺乏罗盘仪,船队必须沿着海岸线行驶,才能保证不迷失在海上。
这种原始的航海方式当然很容易导致悲剧性的事故。喜侯爵的船队从未到达过朝鲜,可能被一场台风吹离了海岸线,然后在黑潮(Koroshio)的裹挟下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横渡太平洋之旅。我们相信他们经过了琉球和日本外侧,并向东北漂流,最北可能到达过阿留申群岛,正如14世纪的张翠山等人经过的路线一样。不过这些北极的岛屿是不太适合温带地区的人居住的。因此,喜侯爵不得不继续沿着黑潮向东南方向前进,直到到达墨西哥海岸。
按照海流的速度,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半年之久。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印度青年“派”在西太平洋的一次海难后就乘在救生舟上漂流到了墨西哥,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期间人们可能以雨水和冰块作为淡水来源,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不免还会食人,以免于饿死。不过这对于经常使用人牲祭祀的殷商人应该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无论具体路线如何,最后大约有数十人到数百人的殷商人于前11世纪下半叶在今天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海滨登陆,是可以确认的事实。他们登陆后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建立了初步的殖民地。考古学家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若干古代定居点的遗迹,有类似安阳宫殿的混合夯土宫殿,也有简易的地穴窝棚,其形态与在殷商故址发现的极为类似。
殷商人不久后就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了接触。但“玛雅征服史”这一名称则是不幸的年代错误(anachronism)。当时的玛雅人远远没有兴起,要在整整一千年后才会有初步的玛雅文明出现。事实上,整个中美洲文明正在最初的形成期,仅仅在墨西哥湾沿岸才有一些聚居的村镇,最大的城市在今天的圣洛伦佐(SanLorenzo)。历史上将这些早期印第安居民称为奥尔梅克人(Olmec)。太平洋海岸仍然有大片的不毛之地。这些海上来的难民完全可以和当地的少量印第安人和平相处。
因此,殷商人不太可能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冲突,至少一开始不会。当初步安顿下来后,他们捕杀了一些太平洋丽龟和美洲野牛,并用它们的甲骨进行占卜。从保留下来的卜文我们了解了关于他们生活若干情况,甲骨文显示他们在不久后就从当地的土著居民或“海夷”那里学会了种植玉米和南瓜,并且养殖火鸡作为肉禽——虽然在汉语没有表示这些动植物的词汇,但由于殷商人使用象形文字,所以他们直接将这些事物绘成了图案,一看可知。
殷商人还恢复了向他们崇拜的“上帝”献祭的习俗,用南瓜、玉米和火鸡作为祭品,表示感恩,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节日性献祭。他们如在亚洲的先祖一样进行祭祀,祭祀中出现了从王亥到成汤的商人祖先的名字,也出现了帝辛的名号。更出现了“告于帝喜”的称呼,这暗示我们喜侯爵在到达美洲途中或此后不久就去世了,被他的后人视为继承殷商正统的先王之一。
在那些甲骨占文,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向风神和雨神祈祷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飓风和雨季的洪水是当时居民的主要威胁,也有各种新的动物神,比如被推断为代表美洲虎和金刚鹦鹉的神祇名称。还有一些询问兄妹之间可否婚配生育的记录,可见当时殷商人的人口一度非常稀少。
不过在两三代人后,到了公元前十世纪初,殷商人大概站稳了脚跟,也恢复了人口,开始了“东进运动”,向美洲的纵深地带扩张,与东北方向的奥尔梅克人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甲骨文记录中也出现大量“伐土方”的记载。“土方”本来是在殷商东北的一个方国,殷商人显然是将其应用于美洲的地理方位上了。同时,人牲殉葬的传统再度出现,在宫殿基址下的几个祭祀坑中发现了被捆绑后砍杀的尸骨,从头骨特征来看显然都是美洲的原住民。这些很可能是战争中的俘虏或奴隶。
殷商人的出现解释了美洲上古文明史中的一个蹊跷现象。圣洛伦佐高地的奥尔梅克城市在公元前950年左右被捣毁了,此后文明的中心出现在了拉文达(La Venta)。可以推测,在殷商人迁徙到美洲的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和奥尔梅克原住民发生了最后决战,并摧毁了圣洛伦佐的文明中心。过程一定相当惨烈。
但是,殷商人的这一胜利不一定是武力的结果,也可能是他们从亚欧大陆带来的病菌所致。中美洲的土著居民从未接触过亚洲的病菌,因此完全缺乏抵抗力。在圣洛伦佐附近发现了一些同时代奥尔梅克人的墓地,其中各种年龄层次的人匆匆合葬在一起,但尸骨上并没有明显的损伤,反而很像是大瘟疫之后群体死亡的情景。相比而言,殷商人,正如之后的西班牙人那样,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各民族接触,对于疾疫的抵抗能力就要强得多。
如果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当地原住民可能大半都死于殷商人带来的疾病。不过殷商人的踪迹在这一时期后也消失了。或许他们也和圣洛伦佐的居民们同归于尽,或许他们在胜利后将新的都城设置在了拉文达,在那里采用了原住民的文化,以变化和融合了的形式长期统治着两个大洋间的狭长土地。
无论真相如何,在此后数个世纪中,正如从日本的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转变一样,中美洲也发生了飞速的文明化进程。天文观测的记录,以及类似中国干支的复杂历法出现了,崇拜羽蛇神的传统也开始了,这一独特的神祇形象——长着羽毛的蛇——很可能是殷商人崇拜的玄鸟和龙的合体;玉石文化也迅速兴起,出现了大量的玉石首饰和雕刻,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中国的玉器;统治者们开始修建阶梯型金字塔,学者们推断,这或许是代表祖先之“祖(且)”的象形建筑。
不过在中美洲从未出现过殷商著名的青铜器,学者指出,这可能是因为抵达美洲的殷商遗民中并没有青铜器工匠的缘故。金属冶炼的伟大技艺就此陨落。当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到来之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金属武装的石头文明。
奥尔梅克-殷商的文明形态,在传承了几百年后催生了后来更为复杂而丰富的玛雅文明。然而其早期起源却仍然晦暗不明。它和殷商人是什么关系?其中有多少属于殷商人的传统?在拉文达所发现的陶器上的铭刻文字,是否是甲骨文的某种变体?我们希望将来的进一步考古发现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中美洲的殷商遗民在后来是否曾经和母国之间建立联系?虽然并未有记载,但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对故土的询问:“殷地安?其可归?”表示他们从未忘却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并渴盼回归。这一占卜语言后来变成了许多印第安语言之间的问候,以至于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因为对方不断对他说“殷地安”而将美洲当成了印度。
事实上,只需要继续沿着黑潮前进就可以经由密克罗尼西亚返回东亚海岸。孔夫子是殷商的后裔,当他在华北复兴古代文化传统的努力失败后,曾经宣称要“乘槎浮于海”,即乘坐小船出海,表示他可能知道在海外仍然有殷商的殖民地。而公元前三世纪的邹衍则提出在遥远的海外有广袤不逊色于中国的“大九州”。在美洲的殷商殖民地可能催生了蓬莱、方丈等仙山的传说。秦始皇听说后,派遣方士徐福去寻找,但这位滑头的术士却仅仅到了日本就不愿再前进。
不过中国人探索美洲的步伐仍然时断时续。五世纪的慧深可能沿着同一海流到达过美洲,郑和的船队也可能在哥伦布之前造访过美洲,正如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s the World)中所主张的那样。不过无论这些说法的可靠程度如何,都无法和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这一次伟大碰撞相比——伟大的诸美洲文明本身可能即由此发源。而这部《殷商玛雅征服史》的出版本身即意味着,在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文明交流历久弥新,并不断从自身的伟大根源中汲取养分。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二):文豪也许是段子手,段子手永远只能当段子手
可能我和亲王八字不合,虽然在微博和知乎上看亲王写的段子经常哈哈大笑,但在kindle上买了亲王的大作拜读之后却非常失望。
给没读过的人剧透一下内容,我买的13版里面是有三个故事:《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欧陆儿女江湖老》,《所多玛记》。三个故事彼此独立,各占60%,30%,10%的篇幅。读完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惊讶了一下,怎么还剩小一半的篇幅故事就结束了?而且这故事到底讲了个啥。
个人观点,写书一定要言之有物,哪怕文笔烂得不如一年级小学生的作文,起码作者要清楚自己讲了什么。有的作者,就我读过的来看就是指伍尔夫,虽然写的东西叫人看了一头雾水,偏偏你心里就能感受到作者字外的千言万语,只是点不透,你知道那些话在作者心里,在字里行间的留白,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你知道那里有东西,有作者的思想。就像朋友抛来的一个眼神,你明白朋友肯定心有所指,只是你不明白到底在指什么。但《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就像是作者在周末的夜市喝醉了酒,一边吃着大腰子,一边手舞足蹈的胡言乱语,说了很多话,可是光是听着就是浪费生命。言之无物,充斥一些荤段子,和不知意象的借喻或者和整篇文章格格不入的政治暗喻。
相比之下,后面两篇多少也值回来¥0.99的票价。《欧陆儿女江湖老》给武侠小说套了个圣女贞德的壳子,奇则奇矣,却不是正道。好在小说的故事内核尚过得去,倒是比《殷商》那篇看得痛快许多。但也只能算泛泛。
《所多玛记》是基于圣经故事,塞了一些《银翼杀手》风格的赛博朋克进去,似乎想讽刺什么,但看得出亲王也没想明白该讽刺啥,所以只是一个略显单薄和沉闷的故事。
以上,我只能给1分。祥瑞御免~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三):地藏天使卡迭颂
正文倒罢了,打动我的是最后一个短篇。
上帝欲毁灭所多玛,派天使检查城内是否仍有义人。天使发现全城杀盗淫妄,只剩一个“光明侠”不屈不挠地试图感化众人,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刀下。
看看新闻,也许会觉得,所多玛并不是一个神话。
面对如此五浊恶世,上帝的处理方式是:毁灭之。而佛菩萨的方式是:救度之。
记得有一位菩萨,见到地狱狱卒对罪人极为凶狠,很不忍心,问,你为什么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呢?
狱卒回答说,我最初也不忍心,每次罪人业报苦尽,要离开地狱往生他处时,我都谆谆告诫他们:地狱的苦实在是难以忍受,你今日得以脱离苦海,可要好好改过自新,止恶行善,不要再回来了啊。可是那些人完全不长记性,刚出去就撒了欢地造恶业,很快又回来了。这么久以来都是这样,既然他们自己要往火坑里跳,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对他们慈悲了。
地藏菩萨昔日本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同样,天使卡迭颂甘愿随着所多玛一起沉入地下,继续凡人“光明侠”的心愿来救度众生——“只要地狱里还有一个义人在,我就不回天国。”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如果不能救度众生,我要永生干什么?
在这个世间,能够看到这样的菩提心,即使只是在一本虚幻的小说里,也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四):一本正经地胡说九道
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非常好玩的书。
除了好玩以外,如果想要读出点其他的味道,也不是不可以,看各人的联想力。所以也不能说,这是一本纯粹好玩而没有思想的书。
无论是娱乐性还是思想性,都是考较功力的。
我注意到马伯庸,是因为河北那家著名的博物馆,而读他的书,这是第一本。
除了佩服,实在说不上别的什么。
我读书很杂,除了专业书以外,也读其他的很多书。有时候,书只要好玩就够了,如果再加上一点让人回味的东西,就是好书。只是好在哪里,有时候,这事不能细说。
单说好玩的部分,看着作者一本正经地瞎扯,语言、故事,如同东北乱炖,看上去煞有介事,吃起来有另外的美味。
我特别欣赏目录,机锋百出,文采斐然,知识的渊博面,丰富的想象力,展现无疑,“知此知彼,百战不Die”实在要让人捧腹大笑,有些欢乐,是唯有文字能够带来,因为如果用视觉化来展现,反而较难,文字有种直观的感受,我为我读懂这里面的大部分幽默而感觉欣慰,对于读不懂的那小部分,我明白属于我知识结构中需要补充的部分。
其实即使不这样深究,这本书读起来都很有趣味,深有深的读法,浅有浅的读法,浅层阅读也许更能带来快乐,因为有些事情,的确不能深入思索。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五):关于我所读到的《殷商玛雅征服史》
不得不说,《殷商玛雅征服史》是一本欢乐而睿智的好书。
在我小的时候,接受了许多公式化的叙事方式,很多时候都是故作深思,言之无物。不知道是应该归咎于当初那个禁止我看课外书的小学班主任,还是埋怨当初那个不够争气的自己,为啥没有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看书的权利。呵呵,不过也没办法,尽管小学四年级前看了很多书,但也旷了不少的课,逃了不少的学,好像这眼睛也是因为那时候电子游戏打太多而近视的。到初中的时候,对课外阅读也就没多少兴趣了,考虑最多的不过是怎么练好英语,半夜三更听敌台听得累了,才会拾起几本书看看,因此睡得晚。现在吃再多也不见长肉,说不定跟这还有点关系。同时,最应该锤炼的中文写作也没怎么进步。因此而形成了现在的两大遗憾。
看完《殷商玛雅征服史》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阅读,怎样才能在读书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马伯庸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虽然《殷商玛雅征服史》仅仅是戏说,用来戏说的绝大部分历史片段也是广为人知,但要以戏谑的手法将这些片段用到自己的演义中,改成现代化的语言,甚至穿插一些当代的术语,凡人如我是肯定无法胜任的。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伯庸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功夫,还能看出他在职场上经受的磨炼。
借古讽今的手法并非鲜见,但能同时给读者如此行云流水的娱乐,实属不易。思路广一下,马伯庸在创作《殷商玛雅征服史》的时候,似乎是将自己的读书笔记摆了一地,然后跟个泥水匠一样把这堆东西给搅和了一下。当然,他得是个非常高明的泥水匠才行。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六):殷商玛雅征服史:快餐式阅读
与往常读小说一样,拿起来就放不下。一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读完。(如果读专业书也有这种兴趣和速度,那该多好啊)读完以后(和读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佩服作者的想象力,以及把不同事物通过这种想象力杂糅到一起的能力。作者的涉猎十分广泛,而且不管写的是真是假,都让人觉得他对这些方面有不浅的研究。
作者煞有介事的写着每一件事,乍看起来像是在讲一段战争史,但是细读又发现原来只是读者杜撰的荒诞故事。甚至连本书的前言都是杜撰的——读到一半才确认这一点——其实从第一句开始就已经表明对于书中写的每一句话你都不该当真。
因为作者在书中犯了不少逻辑的和常识的错误——看起来不像是他故意的,因为即使是这种荒诞小说,也该遵守起码的逻辑和常识,比如东南西北和前后左右的关系。但是书中有好几处这样的错误,所以他故意讲故事的时候,又会让人产生疑惑。就像看前言,直到看到“殷地安,其可归”的故事,我才敢100%的确定这原来tm的是故事。看看,我就是这么好骗。
虽然明明知道多数内容是调侃八卦侃大山,大概是作者写的太一本正经了,读完这本书会有一种历史和荒诞分不清楚的感觉。西游记也算是荒诞小说——和正史相比,但是读完了不至于会产生这种感觉。
这篇小说并不长,故事也简单,没有多少悬念和高潮,但是杂糅了太多的东西,适合网络青年阅读。
总而言之,这是一顿好吃的快餐。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七):胡言乱语见真谛
马亲王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一本正经的扯淡,一本小书拿在手上,饭后2个小时全部读完,读到最后和飞机上的小男孩关于作家的对话不禁莞尔。
最搞笑的就是势如破竹的殷商军队看到胖了流油的女王后整个军队崩溃的那段,精神的崩溃远比身体的折磨更加可怕。
对于SM的解读也让人捧腹,S与M的最初来源并非英文,而是十分典型的殷商象形文字;S是鞭子的象形,而M显然是一尊向上撅起的屁股。
虽然情节荒诞,但马亲王探讨了宗教和政治、王权和神权的关系,不多做解读了,建议大家还是看一看书吧,有时候一笑而过也不错。
《殷商玛雅征服史》读后感(八):玛雅文化的普及
殷商玛雅,两个关键词,吸引住我的视线。好书的一个特点就是阅读飞快,这不,刚拿到手中第一时间就已看完。
阅读之中,让不有种想查询资料的欲望,在书中提到的几个玛雅古城真得存在么?想想是部小说,随他去吧。只是书中不断出现以前获知到的历史的影子,莫非真的存在。
其实自己对玛雅的历史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只是玛雅文化这个名词早就存在脑海之中。像金字塔的知识,心目中只有埃及的知识。玛雅也存在着那么多的金字塔,而且和埃及的金字塔并不相同,了解哦。
在阅读之中,常常会发出微笑,比如当殷商舰队到达南极洲时,看到成群的企鹅站立在岸上,被舰队指挥误认为是准备妥当的敌人,当企鹅飞跃入水后,被舰队指挥误认为敌人开始从水中进攻,哈哈,这太有趣啦。类似的内容很多哦。
书中阐述出的王权和神权也非常有意思,凭借着神权(祭司),普通人也可以一步步掌握王权,建立一个稳定的机构。那段政治和宗教的描述,实在是太经典啦。一语双关,回味无穷!
书中,现代的词汇不断在书中出现,比如公共关系专家。第一眼看见还以为看错啦,待细细品来,原来暗指宣传策划的人员,或是心理专家。在舰队中配置该军种,及时解决部下的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