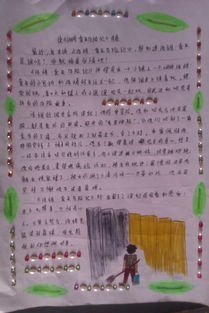《异端的权利》是一本由[奥] 斯·茨威格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元,页数:2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总习惯在深夜阅读,略去繁忙不说,随手抓起《异端的权利》,几月之前买来,因为太好不舍得一口气读完
第二章
“教规”
当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进入科纳文门时,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无数的心灵,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民,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这是欧洲的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施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为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
第七章
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不容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么有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数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他人画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什么他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像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卡斯特利奥为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赛维斯特,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敌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以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么?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是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我深爱反问句的力量
为什么,先生,你就不懂得反省自问呢?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二):评异端的权利
有个朋友某天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天主教几乎没有什么派别,而新教派别却多如牛毛。我说恕我孤陋寡闻,还望赐教。
真别说,和我这朋友一聊,见识还真见长。
天主教和新教最本质的区别,其实只是对《圣经》的解释权。天主教教义认为,《圣经》只有神职人员有解释权,而基督新教则相信人人都可以去解释《圣经》。
解释的人越多,吵架的人也就越多;就好比一锅饭分的人越多,斗殴的人也就越多。
人身攻击是吵架发展一定程度所表现出来的高级形态,而人身攻击的内容之一,就是把被攻击者视为“异端”。
读史者往往会有一个误区:但凡讲到宗教改革,就觉得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新教领袖一定是正义的一方,而罗马天主教廷的一帮则是大大的混蛋。然后后者竖了一堆火刑柱,想让前者统统变成烤乳猪……
而事实是:虽然火刑柱有的的确是后者为前者竖的,但实际上,前者把后者做人肉烧烤的几率并不见少——甚至还多。更何况前者各派别之间还有“相煎太急”的优秀烹饪传统。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历史不是单纯的正义与非正义,改革未必全好,守旧也未必都烂……当历史教科书正在毒害当今纯真青少年分辨真相的能力的时候,我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愚蠢到就摆出一个“好人同坏人作斗争”的故事,然后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它就是历史。
《异端的权利》是我上大学时候看的一本书,它站在一个持相异宗教观点者受到新教徒迫害的角度,让我们重新审视对待历史的态度。
卡斯特利奥之于加尔文,一如茨威格之于纳粹。
这让我想起文革时“雪夜读书无人管”的豪迈。
即使是在思想暴力的无情摧残下,我们的心,仍旧是自由的。
让我不免感慨
原来公知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只要把引言倒背如流就好了
什么?
不,人们不会来询问更多史实细节
要么认为结论是如此明显无需置疑
用不着知道卡斯特里奥或塞尔维特
不,我并不是在挖苦
史实或公知
民主或自由
摘自某美剧:
答:它不是。你问的什么狗屁问题。
我从不指望一种价值观永不犯错
于是,一件事真理到了极点也突然变得很可疑了
书评是什么听起来好可怕
嘿,你说加尔文这货在这个时代,算是异端么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四):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异端的权力》一书以三个人物作为全书的链接点,道德和现实世界的独裁者约翰·加尔文,当然主角,西班牙的跑龙套——米圭尔·塞文特斯,以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上演了一出骑士大战风车的戏码,死在了日内瓦的火焰之中,却成就了二号主角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辉煌的一生以及后世的荣耀。
当改革者褪变为独裁者,要想保住自己的成果,为其所厌恶的暴力与恐怖手段成为维系的不二法门,加尔文完美的演绎了这一逻辑,驱逐日内瓦的反对者,从市政委员手中夺取权力,将敢于不敬畏者投入监狱,利用宗教教条编织一张无缝的天网,拘禁这个共和国人们所有的生机、思想和自由,最后,上帝的归凯撒,凯撒的归凯撒!
塞文特斯则是以西班牙固有的顽固和暴躁,继撕破天主教和新教两派的脸面之后,居然一头撞向了仍被新教徒们认为是改革者,对抗天主教的英雄——加尔文,想着利用《基督教原理补正》(《基督教原理》为加尔文所著,是日内瓦改革宗教的教条性著作)来叩开日内瓦欢迎的城门,结果则是天主教没有完成的事被日内瓦新教独裁者做到了,塞文特斯只有在火柱祈祷上帝,以示绝非异端的份了!
卡斯特利奥,作为加尔文在道德、宗教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持有完全不同的宗教理念,“如果需要你的鲜血染上我的衣服,那么我宁愿自己流血”,宗教宽容的思想贯彻了他的一生,事实上,改革者的血液流遍了卡斯特利奥的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对付貌似强大的前改革者,需要的仅仅是罗列出加尔文以前所写的只言片语,“处死异端是一种犯罪。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更是违反了人道的原则。”
人文主义者在任何一个时代,无疑都是奉行和平主义,立宗开派,结社成党,以暴力对抗暴力,以恐惧对抗恐惧,从来都不会是他们的选择,自然,暴力与恐怖支撑的独裁会相当长时间的处于上风。但,纵然历史无暇顾及正义,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卡斯特利奥借助上帝,在失败前一刻进入了天堂,加尔文则在整个西欧筹划着人间的伊甸园直至死去。
许多年之后,卡斯特利奥的宽容盛行,加尔文的宗教被改革,互相排斥的两极被改良合并,开始在曾经的罪恶之都日内瓦枝繁叶茂,而现代自由主义,这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开始在坚韧的清教徒聚集地,美利坚合众国、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荷兰孕育、生长。
一个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却无权去毁灭另一个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比任何的教义都更神圣!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五):异端的权利
作品可以看作房龙《宽容》的现实生活版本。 其实比起传主卡斯特利奥,我更关注的是加尔文。现代社会可能非常难以想像会出现类似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社会。虽然政治上的集权独裁统治屡见不鲜,不过一个出身平平的宗教牧师能够做成这样令人不解,就是希特勒也是仰仗着国防军和纳粹党才得以建立统治的,从这点看加尔文果然称得上“人杰”。他也算“开创”了现代独裁统治的雏形。 当然作者出于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是极端痛恨这种统治的,所以才有着这部作品的诞生。 塞维特斯事件可以说是加尔文犯得最重大的错误,他对一个没有管辖权的外国人实施了审判并处于火刑,这是作者所无法接受的,而传主卡斯特利奥也因此对加尔文进行了“笔讨”。当然我现在来看,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加尔文,因为所谓司法管辖区之类的,是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并且是民事概念。对于加尔文这个自认为“神使”的宗教狂热份子来说,应该是“无关紧要”的。说难以理解加尔文的只不过你不是那种人罢了。正如“异端的权利”这个书名本身,任何极端份子都有着自己的“权利”,而真正良好的社会就是扼制这种狂热伤害其他人的正当权利。这也是此书真正的意义所在。如果仅把它看成攻击加尔文或者攻击宗教以及其他的不宽容个人觉得浅了。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六):茕茕孑立的抗争
不可否认的是,本书具有感情上的偏向性。
从古至今一直未变的是,当权者大多知道,最易产生依赖的顺从方式是盲从。所以任何的独立的理论体系都不能存在,因为依赖会因此而瓦解。所以说,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让头脑清醒的人被统治,无疑要奉献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抑或下放更多的权力。
从古至今真正的伟大斗士很少,大多数个人往往是很沉默很从众的。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多么软弱,而是上位者对权力的使用即使造成了伤害,只要身边的人和他们一起承受着伤害,只要这些伤害还在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就很少有人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第一个出头反抗。不愿意打破既定的规则,也许可以视作沉默螺旋的另一个表现方式。
即使有人第一个站出来,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孤独地为理想战斗的。没有人站在他的身边,因为理解他的人没有勇气与他并肩,更多的人不理解他,鄙视他,孤立他。这些人对于独裁的感觉是麻木的,其他人的悲惨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甚至有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把自己的悲惨同等地转加于他人身上。
其实更进一步来说,人大多时候都被自己的趋利性所统治着。加尔文铲除卡斯特里奥是为了既得的权力,人民的沉默是不愿意为了他人的利益或自己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放弃更多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候法学家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帮助人民,而当他们得到所需时就站在了统治者的一边。甚至我们可以说所谓民主也是一种集体性统一的利益需求,民主的方式是用多数人的需求来压制少数人的需求,从而获得少数人所拥有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中多数人的需求是合乎道德的。而当需求和道德相悖时,往往就形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然而不论是在黑暗的专制,或是被异化的民主中,卡斯特里奥们总是茕茕孑立地在无可逾越的沉默里抗争。他们也许成为时代的异端,承受精神丰富和现实孤独的反差,但他们竭力追求,给只看到加尔文的人打开新的窗口。而且,在多年以后,茨威格们会为他们写下动人的篇章。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七):异端的权利?我们的权利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一个慵懒的午后时光足以通读完全书。全书文字通晓流畅,虽然涉及的是欧洲宗教史,但只要对欧洲宗教改革有一些了解,加上书中明白的介绍,就足以明了其中的历史脉络,毕竟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而更像一本拥有强烈自由主义人文情怀的政论文。
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书。可能书中记载的只是加尔文、赛文斯特和卡斯特利等人的经历传记,但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这些可能被人遗忘但不该被人遗忘的历史。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德国纳粹势力逐步兴起,民主社会主义的魏玛政权日渐衰微的时代,当时的语境不予许他直言社会的不公和政权的暴虐,于是他采用春秋笔法的曲笔,把他的经历他的思想用一种几乎感同身受的心理分析方式,用加尔文、赛文斯特和卡斯特利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表现出来, 并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题目:何以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教徒们会去迫害和他们同样信仰的新教徒?何以被天主教以异端为名迫害的清教徒,又以异端为名迫害他人?何以一位主张心证圣经的宗教改革者,会虐杀一个仅仅对圣经有不同解释的虔诚者呢?这样一本有着丰富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书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作者的论点就过于空疏,如果仅仅当成历史来看,可能未必了解作者微言大义的苦心。
这是一本代入性很强的书。这也说明了极权统治无论挂上什么样的羊头,其本质都是愚弄人民,继而通过思想上的专制,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的专制的。如果把《圣经》换成《我的奋斗》,把加尔文换成希特勒,把日内瓦换成柏林,把赛文斯特换成犹太人,把火烧异端换成送入集中营,那它说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的纳粹德国史;如果把《圣经》换成《斯大林全集》,把加尔文换成斯大林,把日内瓦换成莫斯科,把赛文斯特换成托洛斯基、季诺为耶夫和布哈林,把火烧异端换成肃反,那它说的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如果把《圣经》换成毛泽东思想,把加尔文换成毛泽东、把日内瓦换成北京,把赛文斯特换成55万知识分子,把火烧异端换成反右、反右倾和文革呢?丧心病狂的历史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赛文斯特是不幸的,出生在那个野蛮的时代是信念执着者不可避免的悲剧;赛文斯特又是幸运的,虽然惨遭虐杀,但有卡斯特利奥这样有着良知和智慧的学者为之辩护和呼吁,没有落到“暗暗死去”的下场。卡斯特利奥的辩护是精彩的,一方面固然有加尔文愚蠢的助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卡斯特利奥坚定而宽容信念,严谨的逻辑与身体力行的上帝之爱。文章后部的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的精彩论战,与其说是历史的讲述,不如说是作者对现实的无奈的呐喊。
如果《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只是一味的控诉,可能其中的批判力量会减弱许多,因为那是几乎500年前的往事,但作品的不朽在于书中不但有着对加尔文独裁统治的尖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卡斯特利奥说出心中的理想,一个宽容的和解的不以思想分歧治罪的世界。那些以宗教或者主义为名义迫害异端的加尔文们是有罪的,以野蛮暴力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可能会一时得逞,但历史的审判必将会将他们放在应该的位置;那些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者也是有罪的,认为异端或“极少数”因为不和主流,或不被当局所允许所以是有罪的,不但逻辑混乱,而且也埋下自取灭亡的伏笔: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食肉者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划入一小撮的异端里,做着帮凶的人们怎么就能奢望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献上神台的牺牲?被神化的加尔文大师们有着历史伟人的光环,但我们也要看到辉煌形象的背后那黯然的血色;而被妖魔化的卡斯特利奥们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战斗,认同当局承认鼓励的观点当然是务实,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成为异端而不被迫害的权利,异端不是罪行,而是我们的权利。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八):重审异端与权利
铲除异端,是为了保卫信仰,拯救真理。
但,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真理吗?或者说 一个人能够完成垄断真理吗?
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有限性 我们每个人的判断都可能标示着错误,绝决的惩罚也可能意味着错杀了真理
唯一而排他的真理 就像一道穿越历史的魔咒 充满了无限的神秘诱惑。
求知的人们纷纷前来,无数的人至死都在默默追寻着它,也有无数的人宣称已经占有了它
约翰 加尔文正属于后者
用荣格的话来说 他正是内倾思维型的典型。
倾其终生都在追求真理,并且完成了一套严格周密的神学体系,
在这里 我不禁要打断一下 问一句 真理到底是什么呢? 独一而排他 没有违背二律背反 这也许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无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毕竟生活是多面而复杂的。
朝着相反的方向继续运动,我们就可能滑入相对主义,但毕竟在没有绝对的证据之前,还是应该保持知识的开放
而加尔文这位内倾思考型就生活在他逻辑的自闭中。当加尔文将属于他自身的规律强加给世人时,他也就否认了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可能性。
完整的真理 也许正是世界上每个人意识的相加。
我们每个人只能孤独的生活于自我之中,在他者这个巨大的未知面前还是避免狂妄的武断,保持一份谦卑。更多的去尝试了解。
宗教的过去也曾教导我们保持谦卑,当信念变为一种狂妄。悲剧也就随之发生了。
本书的作者茨威格
我不想过多的拿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 在我看来这两位作家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茨威格 的文风有些过于阴柔,描写有时会显得赘叙。但对于习惯法律这种限定性语言的我,当然甚是喜欢。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苦难的哲学与灵魂的拯救,而茨威格基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写的都是 激情的爆发 爱的渴望,当然也难免情感泛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灵魂更深层的一面,而茨威格写的就是情欲。我认为是无法比较的。当然我更喜欢茨威格一点。
我也不想再过多的去批判加尔文,因为我很欣赏这位日内瓦的教皇以及他的思想。
但历史让我必须认清他的污点。这些缺陷也不应让我们否认他的功绩。
卡斯特里奥在法庭上对加尔文的那一段辩词
让我想起电影《浓情巧克力》里的一段布道词。
加尔文对自身年轻时候的自我背叛
就像耶稣基督到了老年(复活后)在末日再临,执着于对众人的严苛审判。成为神以后他只忙于去不断的惩罚。我们应该回想在耶稣年轻 还是人身的时候,那个时候 耶稣尚没有神力加护 脆弱而易受伤害 却也更懂得爱与宽容。也许我们都走得太远而忽视了这一点。
圣经的故事有时候正像一个隐喻。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九):异端必须压制
这本小册子写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则是全民“狂欢”的文革之后,都有那么点应景的意思。估计文革之后的那一代人阅读此书时应该会非常震撼,人类的历史悲剧总是这么残酷的重演,演员换了,道具换了,但是剧情不仅没变,甚至更残酷了。我们的伟光正掌握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嘴唇稍微动一下,那你就成“异端”了。由于东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传统,你会发现这里的统治者比西方的加尔文们更能为所欲为。
“这不是想缚住教会的手脚,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开地撒播他们心里的想法”,这是多么熟悉的论调,我们不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只是想阻止“有害信息”的传播。统治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这个荒谬的逻辑去压制“异端”。悲哀的是,群氓们却认同这个“逻辑”。因为大多数人其实不喜欢自由,他们渴望“秩序”,因为这样就无须面对责任,逃避“思考”的痛苦。这就给那些野心家、理想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他们一旦取得了权力,几乎无一例外即被证明他们是恶劣的骗子,权力促使他们利用他们的信徒去攫取更大的权力。
最近心态比较消极,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也是“悲观”,就无病呻吟的发了点感慨,塞维特斯、卡斯特里奥和茨威格,我向你们致敬!
《异端的权利》读后感(十):我们需要信仰和勇气
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勇气
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弄懂了这三个问题,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确实,如果不读这本书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加尔文先生是如此残暴可怕的一个人物。高高在上的加尔文,总是和神圣挂钩,他是宗教界的英雄,推进宗教改革,和马丁路德等人平起平坐。这本书让我对中世纪的宗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要感谢茨威格先生。
记得当年在苏丹的时候跟一个德国观察员专门聊起来ZWEIG先生。我曾有过学德语的热情,就是因为他。在我看,茨威格先生和安德森一样,都是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们洞悉人类的灵魂,洞悉人的想法,并且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安德森倾向于抽象,茨威格先生更倾向于具象表达,生怕一点点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