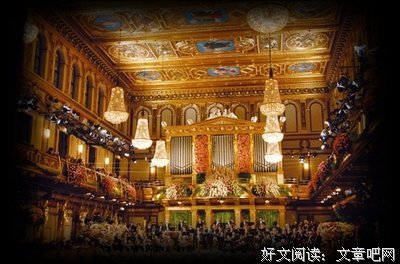《世纪末的维也纳》是一本由卡尔·休斯克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41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一):【读品•细读】子默:以小细节读解大历史
作为历史学家,在一个宣称“历史已死”的时代做学问当然不那么怡人。那么,是一脚踏进后现代的洪流,还是以精英的姿态故意视而不见,或者如卡尔•休斯克这般,在其饱受赞誉的史学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开篇即承认:“现代人已然对历史漠不关心,尽管历史曾被视做连续提供滋养的传统,现如今早已无甚价值”。从战术上说,对敌手的重视,似乎已经赢了几分。引入注目的是,休斯克对19世纪末的维也纳各种文献材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小叙事中见出的对大历史的思考与体验,为文化史领域又增加了一本精彩易读的著作。
不得不首先指出书名翻译的瑕疵——原著的副标题“政治与文化”不知何故被省略,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作为本书的基本主旨而贯穿始终,这样被略去,难免轻率。“当政治问题变得具有文化性的时候,文化问题也就具有了政治性”——休斯克这样表述著作的思路,并落实于具体的历史人物,以施尼兹勒、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克利姆特和瓦格纳等人串起写作线索,按照各自的文化意蕴,在文学、心理学、建筑和艺术等领域得到细致的展开。七个单独的专题,均可分别阅读,看似毫无关涉,但仔细阅读便可发现,这些人物之间不仅有着人际上的联系,文化上的血脉关系才是根本所在:他们都是自由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也就是反抗的一代,这是时代打在他们脊背上的烙印;而个体在政治与文化的二重奏中的迷茫与定位,今天读来,依然不陌生。
正如David A. Hollinger指出的,这种织网般的爬梳,“对史学自身做出了有力维护”。这显得似乎又是一本难啃的大部头著作,恰恰相反,其写作形式,却是一个个可读性极强的人物故事。以克利姆特为例。说起先锋艺术家,大多数人总要皱皱眉头撇撇嘴,他们要么造型奇特,要么生活另类,还折腾出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于是,先锋往往与“出格”联系在一起,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伦理背道而驰。只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先锋艺术家出尽风头的一面,但风头过后,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叹自然少有人倾听。
克利姆特,这位奥地利“分离派”运动的领军人物,遭遇大抵如此。其建筑装潢师的出身,使他在维也纳自由派分子建造环城大道之时一展才艺。初始,克利姆特通过将古典风格和现代维也纳文化杂糅的方式,投合了自上层阶级到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一时间声名鹊起。然而,在自由主义政治的危机之中克利姆特转向了既令他声名崩溃又使他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抽象派风格。对本能生活的探讨,对情色生活的挖掘,对女人性爱能力的展示,克利姆特向现代人高举镜子,试图将性从道德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哲学》、《法学》和《医学》三部曲的问世,成为对自由主义乐观理性的诅咒,也使克利姆特与整个维也纳成为殊死对抗的敌人,政坛的压制,公众的谩骂乃至职业的疏远,先锋艺术家的十字架,不那么容易背负。
然而,克利姆特不过是历史的替罪羔羊。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分子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掌握了维也纳的控制权,但历史意识的解体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已经初露端倪。正如休斯克指出的,奥地利社会未能够尊重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秩序和进步,自由派分子成功地将群众的政治能量释放出来,可矛头对准的却是自己,而不是老对手贵族阶级。日耳曼主义者斥他们为民族主义的叛徒,因为自由派分子出于多民族国家利益的考虑甚过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扶植;经济放任政策的初衷,却唤起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天主教作为新教的对头被从学校和法庭中逐出,却成为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卷土重来;甚至,令他们摆脱压迫、获得机会、融入现代的犹太人,也对恩人背弃不顾,因为自由主义逐渐丧失阵地的事实令他们受害,于是,最自然的回应便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
文化上,奥地利贵族阶层的没落是由于外族的侵入而非本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所致,这导致了自由派领导人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兼之自己暴发户的出身,面对贵族阶层的高贵和优雅,便已有了无法抹去的文化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反映在文学、建筑、绘画等各领域,虽然自由派执掌了政府权力,却全面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甚至以能够依附贵族文化为荣——这自然引起了在自由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诸如施尼兹勒、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以及克利姆特等年轻人的不满,因而,在本阶层内,自由主义已是四分五裂。
当然,事后诸葛亮总比当局者来得轻松很多,克利姆特不会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作出诸如此类的分析,从而给自己找一个坚强的精神盾牌。相反,他几乎放弃了之前的艺术风格,成为一名大众艺术家,“我受够了审查。我要寻求自助。我要逃脱出来”,他退缩到私人世界,干起老本行——这一次,是为维也纳上流社会服务的画家和装潢师。他有了稳定的艺术上的资助人,当然,也不再受到伤害,因为他不再先锋。
那么,对施尼兹勒和霍夫曼斯塔尔来说,个人在一个行将解体的社会里具有何种性质是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关注焦点。施尼兹勒走向在一个价值取向混乱的社会里常见的一个产物——价值真空,“他借助粉碎幻想来提出问题”;霍夫曼斯塔尔则将美领向朦胧模糊的非理性王国,帮助迷路者们走向注重实干、立足社会的生活。建筑师瓦格纳和西特在立足于公众还是功能至上两个领域,分别质疑他们曾经心仪的自由主义文化,尽管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孤独;正在中年事业危机中煎熬的弗洛伊德,拿起了精神分析的武器,终于以弑父理论为自己赢得声誉,尽管臭名昭著,却就此否定了为自由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理性文明;甚至连昔日自由主义政坛的三位领军人物,也摆脱了自己的政治出身,利用贵族文化传统中力量,顺应现代群众政治的追求。自由主义溃败之地,种种辛酸正如休斯克所道:“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抗着奥地利自由主义文化,因为对于一帮仍旧十分怀念前理性主义社会秩序的民众来说,这种文化只能满足头脑,但却使灵魂无比困苦”。
“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布克哈特的历史观引起了作者的共鸣,这提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即是回应当代。这不仅因为,当代政治文化的发生学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前,更在于,当代政治文化的危机可以在19世纪的维也纳,这个似乎总是以艺术来装点自己的繁盛的地方,得到启示。
二战后的十年,欧美国家陷入了奇怪的悖论: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迅速累积,另一方面是普遍出现在精神领域的匮乏感和空虚感,正如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里引用战后普通美国人的话:“我想乘一乘会用原子弹把西方文明炸毁的飞机”。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知识界曾经信奉的启蒙理想大大削弱,自由派和激进派“几乎是在无意识间,就调整了自己的世界观,以顺应不断降低的政治期待值”。学校里的大学生们,尚未步入社会,便已经对存在主义的一套烂熟于胸。所有的信息都在表明,后自由主义时代依然来临,在六八年五月风暴的狂轰滥炸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于是,蒙娜丽莎被画上了两撇胡子,小便池进入了艺术品展览,目力所及的任何普通物品可以在一夜之间挂上艺术的招牌。我们刚刚念叨着现代主义的晦涩,一种名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来到眼前,我们正在努力借助着大段大段的注释啃读艾略特的《荒原》,眼前却来了一个诗人,他说,嗨,别费力了,随便打乱一段文字,重新组合词组,瞧,诗就制造出来啦!这似乎没有道理,却也无法轻易辩驳。
世纪末的维也纳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百年后,在20世纪的80年代,一位美国学者因时代历史的碎片化感到困惑,又认为对此不能再泰然处之、不管不问。于是,他将视线投向那一个世纪前以繁华与喧嚣闻名的艺术之都,试图找寻“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中跟这些观念的紧密联系,及其含义和重要性”。因为,“在文化创造者中间,这种思想和价值全面而突然的转型,表现了人们共同的社会体验,也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世纪末的维也纳,提供了这样的背景:在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中,我们在寻找未来的路——这是宿命,也是希望所系。
[美]卡尔•休斯克著:《世纪末的维也纳》,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28元。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二):书写的变奏曲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卡尔·休斯克教授表面上针对的是特定时空的具体个案,然实质上,作者格外强调的是历史的延续性和史学研究的整体性。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当下的参照体系,时代是在摆脱历史桎梏的努力中实现蜕变的。19、20世纪的维也纳处于新旧激荡的时代,在社会与文化嬗变的混乱格局中,“现代”悄然孕生,逐渐成长为左右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的精神资源。本书的切入点放置在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层面,以此为主旨营造起一个统一连贯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不同的个案得以彼此勾连互相印证。其可行性的基础在于,当时的维也纳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出了革新,整体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文化精英们在各自领域中开掘的同时,具备着一些虽难以描述却意义重大的共同社会经验。于是,本书便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中铺呈开来。
作者对历史延续性和研究整体性的关注还不止于“具体问题”的本身,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史学科学和研究方法的态度上。当发现史学无力整合社会与知识混乱而碎化的事实时,作者试图向其他学科寻求帮助,竟然发现其他人文学科处于同样的尴尬与无奈的境地当中。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学科分化之后,各学科都在纷纷界定自身的知识功能和研究领域,进而导致基础的缺乏,所谓基础是以历史为根本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学科在自我成长中,割断了自身与历史的联系,使得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越来越狭窄。对于文化的多样性,统一的前提或者连贯的准则丧失了。那么究竟是否尚存可能对历史或文化进行概括性的整体描述?此时,跨域研究是必需的,作者在跨学科的过程中,谨慎地对待不同学科生发出来的自主性分析方法。
就方法而言,本书作者的主张与科学史(参丹麦赫尔奇·克拉夫著 任定成译《科学史学导论》(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所关注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后者将科学史分为水平科学史和垂直科学史两支。水平科学史理解为对给定的狭窄主题的整个时期的发展研究,如某个科学专业、某个问题领域或某个智识主题。通常给定了时间界限,就可能分辨出主题的起源和灭亡。垂直科学史则是从一种本质上更具学科际性的视角开始,所关注的科学只被看作是某一时期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元素。这种元素不能和该时期的其他元素分离开来,它和这些元素一起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而这种时代精神恰恰就构成了这种类型的科学史的真实领域。当置身于外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社会进行观察时,我们发现每一个时间点整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假设我们将历史时刻定格,那么历史的发展将成为无数“空间地图”的层叠,只有将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对应起来我们的研究才具有意义。我们试图做的实际上是“水平史”与“垂直史”的重合部分的研究。如何减小侧重时间的“水平史”和侧重空间的“垂直史”各自的局限性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此时,历史主题不变论点(the thesis of invariant historical themes)或简称为不变性论点(the invariance thesis)便成为包含水平和垂直两种特性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组织方式。这一论点认为,可以把历史看成在十分重要的文化分支中的不同时期出现的数目相对较少的恒定主题或思想单元上的变化。思想史不变性论点的一位重要代言人Arthur Lovejoy指出,可以把思想单元比作元素的原子:正如可以把成百上千的化合物理解成几种原子的结合体一样,可以把思想史上复杂而极端不同的形式设想为几个思想单元的结合体。由于它试图整合构成文化的不同元素,并且同时从时间上弄清这些元素,因此这个论点变成防止水平史学与垂直史学冲突的一种尝试。结合不变性论点的方法原理和中古社会分工的特定发展阶段,我们便可以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所有组织做出一个大概的划分,进而分析它们各自的演进特点和彼此之间的互相作用,剖析最终导致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而言,《世纪末的维也纳》为我们践行类似的方法进而从事整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从史学反省与批判的角度而言,卡尔·休斯克虽然采用了叙事性的语言,但作者只是将历史当作研究的对象,在历史本身与历史书写之中,作者一直比较谨慎地限定自身的位置,他始终保持观察者的分析态度。于是,本书不再是文献材料的历史,或者说根据文献材料作历时性叙事史学,而是将文献视作与科学、艺术品同样的外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将其与特定的社会相联系,运用合理的逻辑和有效的方法进行精细的论证严格的推衍,进而解决发自我们本身对于历史的追问。
大体而言,《世纪末的维也纳》追求的都是如何认识一个特定时空下的整体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诸多社会因素如何同时发生变化并互相之间影响着,作者通过个人的呈现,实际上描绘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充当了“关于过去”的观察者,而非“处于过去”的观察者。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克斯著、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
于《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8月。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三):碎裂的乌托邦
这是个看不清方向的时代,时代的混乱局面让所有人感到惶惑不安,是进步还是倒退,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个陷入危机中的时代,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的不协调感、破碎感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找寻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在他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描述到的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精神状况。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汇概括那个世纪末的城市维也纳,我会选择碎裂(fragmentation),一个颇具后现代意蕴的词汇。“碎裂似乎无处不在,”卡尔•休斯克多年后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维也纳的思想史发展状况时说,“每个领域都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体之外,而这些独立出来的部分反过来又分裂成新的、更小的部分。文化现象正视凭着一些概念才固定在思想上的,而这些概念都被卷入到无情的离心变化中。不光是文化的缔造者,即使是文化的分析者和批评者们,也不幸沦为这种碎裂的牺牲品。”面对已经陷入到碎裂和剧变中的维也纳,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怎么办?答案显然已经摆在面前,当然不是任他随风飘摇随风倒,也不是用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帐幕统而化之,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尊重当时的多元化的文化现实,书写出来一部“碎裂的文化史”,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的《世纪末的维也纳》。
这部书细想来拿到手已经三四个月了,厚厚的让人人望而生畏,原本感觉到预期的阅读可能是一种细细的、折磨人的残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卡尔教授的显然不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一部主题涉及到思想史和文化史交叉的大部头著作中,文笔细而锋,文字详实可证,稍微文学性的笔法,不但读起来颇具趣味,而且显露出高雅的人文素养。全书共分为七章,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分别是:文学、建筑、政治、心理、绘画和音乐。但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构建一副历史全景图,所以各个章节又能根据个人的兴趣和需要独立阅读。这本来是此书的一大特色所在,但是有评论者却认为这种独特性的书写是一种缺憾。在我看来,如果这样也能算是缺憾的话,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整体主义者,而且对当前我们多元化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
卡尔教授显然颇为认同布克哈特的观点: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我们能从那个世纪末的维也纳城市中发现什么呢?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挫败;文化领域中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冲突;建筑领域中是立足公众还是功能之上的争论;弗洛伊德“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的提出在心理学上的突破;绘画领域中分离派的成立,并毫无惧色的喊出了他们彪悍的宣言:将艺术献给它所在的时代,将自由献给它所在的艺术。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口号指引之下的自然迸发。这是一座弗洛伊德式的城市,尽管这个城市让弗洛伊德终生郁郁,但是在这个城市中,新的文化创造者们就是不断的通过一种集体的、俄狄浦斯式的反抗来界定自己,这其实已经是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最大的肯定了。“与其说年轻人反抗的是他们的父辈,倒不如说反抗的是他们继承来的父权文化的权威,他们在漫长的阵线上攻打的,是他们从小成长于内的古典自由主义权势,”卡尔教授如是说。
1905年,维也纳的文学巨匠之一霍夫曼斯塔尔写下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感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游移感’,而且可以确知的是,其他时代所坚守的,实际上也是这种游移感。”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霍夫曼斯塔尔的话中很恰当了表露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游移感”不仅仅是打倒传统后的拔剑四顾的茫然心态,更是一种子系文化一旦挣脱父系文化的纽带之后的一种无所适从。借用霍夫曼斯塔尔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成为了碎片,碎片又继续破碎,成为更多的碎片。不再有什么东西,能够允许自己被概念所接受。”又是碎片,看来“碎裂”这个意象已经深深的镌刻在了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整整一代人身上。
其实用“碎裂”概括世纪末的维也纳的艺术各个领域发展的特点注定是不完整的。虽然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时代失去了方向感,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在维也纳这个城市,因政治上的不断挫败,自由主义的失势,致使掌握这个城市的文化命脉的中产阶级短暂性的失落,短期性的集体创伤。但一旦他们意识到无法在政治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转身投入到自己熟稔的领域:文化领域,并在此建构自己隐喻的乌托邦世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而是用一种文化的方式谈论着政治上的压抑,用审美的形式进行着对政治意识的反抗,用无声的画面诉说着自己对政治的不满。以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为例。1897年,克利姆特带领着他组成的“青年反抗军”组建了维也纳绘画史上名噪一时的分离派,他们的纲领之一就是声称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但是到了短短几年后的1908年,克利姆特已经在与社会的交锋中饱受创伤,从历史、时间及斗争的国度中,无可挽回地转到了审美与社会隐退的国度。那才是他最熟悉的艺术乌托邦世界,只有那个国度中,他才是真正君临天下的君王。
霍夫曼斯塔尔的话的确道出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的主题:“与现行的社会秩序较量很难,而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更难。”在一个颓废、混乱、压抑、百废待兴的年代里,用艺术和审美构建一个乌托邦世界,注定是一个碎裂的世界,像一个碎裂的镜片,折射出的却是光怪陆离的真实世界。
思郁
2007-10-10书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四):维也纳1900:最后的华尔兹
现在,或在将来的时刻,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都变了。
都已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叶芝《1916年复活节》
维也纳1900:最后的华尔兹
如果18世纪存在心脏的话,那么维也纳的末世华尔兹舞步无疑是最为撩人心弦。
文学家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急于在政治与精神的悖论中调和贵族传统与资产阶级风尚;奥托.瓦格纳和卡米洛.西特则分别在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上投射时代分裂的政治理念;柯柯什卡和勋伯格游移感官和精神世界,借绘画和音乐的新语重新定位失去的精神花园;信仰“艺术属于它所在的时代,自由属于它所在的艺术”的克利姆特索性创立分离派,追寻“赤裸真理”的踪迹……
是的,这就是1900前后的维也纳。它颓废,它隐忍,它浮华,它克制,它妩媚,它暧昧,它分裂,它热切,它含蓄,它放纵……一百多年后,当历史学家卡尔.休克斯将目光投向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时,不仅为它的璀璨星光感到眩晕,更为那个时代理念的混乱冲突所震撼。
《世纪末的维也纳》算得上的卡尔.休克斯巅峰之作,面对当时维也纳芜杂多姿的文化形态,他毅然摒弃黑格尔式“时代精神”,而是从分别从文学、音乐、绘画、政治等七个不同的角度来临摹世界末维也纳的浮世众生相。
受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世纪下半叶开始,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大概维持了近四十年的统治。奥地利资产阶级与英法相比,既不能完全消灭也没有充分融合贵族阶级,同时又依赖和效忠于皇帝,所以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更早地陷入没落衰败。四十年貌似歌舞升平的岁月背后潜藏奔涌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仅仅取得市区中心中产阶级日耳曼人和日耳曼犹太人的支持,弱势的自由主义者只能一边不得不与贵族阶级妥协共存,一边又借助释放民众的力量来对抗贵族阶级。
四十年来,奥匈帝国脆弱的政治平衡一直走在行将崩溃的边缘,作为议会力量的自由主义者一退再退,与之对应的是由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社会群体节节胜利。到了19世纪末,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曾经属于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的维也纳已经完全沦丧于“民主激进派、反犹太人士、新兴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及最后的社会民主党”手中。
维也纳帝国时代自由而富足的氛围孕育了大批艺术精英,他们构成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主力。此时,往昔欢快的华尔兹已近尾声,民众的喧哗与自由主义的失败使他们陷入一种焦虑、无力、绝望的空前境地。奥地利文化存在道德科学文化和审美文化两个方向,前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后者则更多来自资产阶级的推动。但是自由主义的溃败使得旧有自由主义价值观遭遇幻灭,或多或少,维也纳艺术家们都在迫不及待地作别旧时代,拥抱新价值。因此,世纪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政治与文化的互动,贵族阶级审美倾向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互相纠葛,种种张力恰巧构成了大转型时代维也纳的历史趋势。
一度,拉威尔的《圆舞曲》被视为维也纳末世横死的最好写照。在飞扬的军号、有力的疾奔、甜美的助奏、大气的主旋律之后,一向被视为太平写照的华尔兹演变为疯癫的“死亡之舞”。太平盛世,最大的“兵荒马乱”不过幻灭,政治失意下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宗教,在价值混乱年代,艺术成为尘埃中的救赎之花。
1900年,一个44岁的犹太医生正式在维也纳发表他惊世骇俗的著作:《梦的解析》,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此前《梦的解析》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版,但直到1900年,它开始更广泛进入公众视野,也从此照亮了人类无意识的灵魂之域。启蒙运动让人类明白人应该自由运用理性,而政治挫败感之下的时代危机则无意间为人类打开了心理的大门,开始关注情感与本能。
奥斯卡·柯柯什卡认为现代人是“被判定要重新构建自己宇宙”的人,在一个碎片化的年代,失落颓废成为群体行为。卡尔·休克斯认为弗洛伊德的意义不仅仅在精神分析方面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将政治问题简化为有关父子的原始冲突,这无疑为当时的自由主义同仁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慰藉,让他们能够承受一个无法重振的末世。
伯尔克哈特曾经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
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许正是一种例证,1900年的维也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座弗洛伊德的城市。古典自由主义所孕育的文化精英在不同方向上对传统的抗拒,隐含了俄狄浦斯式的姿态,遗憾的是他们参与埋葬了旧时代,却未必等来理想的新天地。事隔多年,一战结束之后,目睹山河破碎的弗洛伊德在日记中伤感地写下:“奥匈帝国已成明日黄花,我只想生活在维也纳,对于我来说,移居他邦是不可能的。”
世纪末的维也纳,已成最后一曲华尔兹,只存活于记忆之中。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五):譯者怎麽可以如此胡來?
如果說某些譯者看得出是由於自身能力有限在無力地掙扎,那麽這本書的譯者可就是公然篡改原文的意思了。當然,他的假設是讀者手頭沒有原文。
初次捧讀此書,感覺譯文意思還算曉暢通達。不料在腳註裏,我們的譯者開始暴露出其不足。Velasquez(委拉斯開玆)這個名字,在譯本第289頁上,被譯作維拉格!第356頁上,Wien: Ein Fuehrer這本書被譯作《維也納:一個領袖》,書名顯然應該是《一本維也納指南》。
書中的德語引文總是缺胳膊斷腿,Mensch這個詞,在第248頁腳註中
變成了Mesch。此書講述的是德語世界的維也納,Georg這樣的人名,譯者總是以“喬治”處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這些都是容易瞅見的問題,然而把譯本和原文的開頭對照一下,就會發現此書中存在的誤譯是多麽的可怕!
The Waltz, long the symbol of gay Vienna, became in the composer's hands a frantic danse macabre.
譯本:華爾茲本是奧地利歌舞升平的象徵,可在這位作家手裏,卻變成了瘋癲的“死亡之舞。”
好傢伙,維也納被置換成了奧地利,long這個詞顯然就被他用“本”給敷衍掉了,拉威爾從作曲家搖身一變成了“作家”。
接下來,拉威爾寫道: I feel this work a kind of apotheosis of the Vienna Waltz, linked in my mind with the impression of a fantastic whirl of destiny.
譯本:我感覺這部作品是對維也納華爾茲的稱頌,讓我的大腦呈現出命運旋舞的景象。
詞語的意思(apotheosis)和句法被粗暴地推到一邊,“聯係、連接”的意思根本沒有翻譯出來。a fantastic whirl of destiny,完完全全被這個譯者給糟蹋了。
繼續往下看:His grotesque memorial serves as a symbolic introduction to a problem of history...
譯本作:他的這一風格奇異的回憶作品,象徵性地把我們引領到一個歷史問題前……
grotesque翻譯成“風格奇異”,已經不像話,後面這句簡直就屬於天方夜譚了。拉威爾的作品起到了介紹的作用,和“引領到……的面前”這個意思似乎還有很大的距離。象徵性的介紹,與“象徵性地把我們引領到……”的意思也是霄壤之別。
下一段開始:……he does not initially present that world as unified.
譯本作:但他並未完整地把這個世界呈現出來。
明明是他(拉威爾)起初並沒有把那個世界呈現為統一整體,譯者的偷梁換柱讓我瞠目結舌。“起初”這個詞,索性就消失了。
再往後有一句:Each element is drawn, its own momentum magnetized, into the wider whole.
譯本作:每個元素、甚至每個元素的動力,都被吸收融入到更大的整體中來。
“甚至”我不知道從何而來。its own momentum magnetized這一部分,我們的譯者分明是在糊弄讀者。
書的第一頁上就出現了這麽多錯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繼續閲讀譯本。而譯者,據扉頁上的介紹,是研究英美文學和西方文藝批評的博士!
嗚呼哀哉……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六):关于书评的评论(转载)
云中君
引用:
--------------------------------------------------------------------------------
最初由 木兮 发布
《世纪末的维也纳》更多的书评可见: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18766/
云偶推荐了这本书,有人认真的看了吗? 也把读后感贴到这里就好了
--------------------------------------------------------------------------------
木兮,我到你转的豆瓣上看了那些评论,除了认真纠正译文错误的那篇,都比较一般。尤其是在《读品》上的那两篇,更是胡言乱语,对原书的史学特点和维也纳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没有什么了解。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七):俄狄浦斯式的希望:不一样的社会和思想史
卡尔•休斯克基于历史学家的敏感性,观察到“现代”概念宣扬的自我重构所具有的俄狄浦斯式的根源,其所宣告的“历史之死”正是这一情结的突出表现。基于对“现代”这个天生革命性概念的探究,休斯克选择了“非历史文化”爆炸式出现的时空——世纪末的维也纳——为探究对象,期望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探索古代(ancient)向现代(modern)转型的肇始。
正如作者所说,从尼采之后,碎裂成为了文化的主题。在无限创新的离心变化中,构架“文化”框架逐渐成为不可能的任务。文化的每个构成分支都从自身出发构建了自主的分析性范畴,面对这样的困境,休斯克提出史学家必须放弃对通用标准的渴望,而向各个专门学科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织工”:以历时为经线,以共时为纬线,以各个学科的分析范畴为纱线,织出经久耐用的布来。因此,他尝试通过以共有的社会体验和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为基础,将文化活动的不同分支:文学、城市规划、造型艺术等,凝聚在一起。而这共有的社会基础正是世纪末的维也纳的社会变迁。下面通过对每一章的简短梳理,来领会那一特殊时空的光怪陆离的真实世界。
背景——自由主义文化的政治危机
从抵制巴洛克专制的光辉胜利,到被现代群众运动、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击垮的短暂历史中,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文化一直充满危机,资产阶级期望通过强调审美的文化之路与贵族阶级进行社会同化。然而,“维也纳资产阶级在吸收审美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贵族阶级在没落时没有撒手的集体等级意识和功能意识。”“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P7)因此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90年代趋于集中,资产阶级在同化贵族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审美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带来了自恋和对生活情感的夸大。自由主义者原本的理性被大大削弱,却未消失,所以导致了其自身的的矛盾感:“对艺术和感官生活肯定中间,却夹杂着负疚感”(P8)
在这一社会背景中,阿瑟•施尼茨勒和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面对着现代政治考验中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的瓦解的现实。他们都认定,在旧文化的残骸中,心理意义上的人已经出现。不同的是,施尼茨勒从传统的道德科学角度切入,虽具有社会学洞见,却染上了悲观主义情绪。而霍夫曼斯塔尔通过探寻从艺术神殿通往围墙之外的出口,找到艺术作为唤醒本能的途径,并将其运用到政治艺术上:即通过参与整体仪式,来疏导非理性的情感力量。
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构筑环境的现代思想
以环城大道为主的维也纳大改造,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在19世纪后半叶前期是上层阶级追逐的对象,但在后期成为了批判的焦点。正如文中所说,“支配环城大道的,不是实用,而是文化上的自我投射”(P25)十多年来的环城大道的建筑功能的转变正是政治在文化上的投射——从军方象征的军火库和兵营,到新专制主义价值观的感恩教堂,再到回应新统治阶级意愿的公共建筑。不同于巴洛克式的新颖的空间概念:其建筑组织连贯的布局原则突出了多面形的街道,形成了内城和郊区之间的社会隔离带。同时建筑风格的多元思想也体现了维也纳资产阶级观念的多元和斗争。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厅、巴洛克风格的皇家剧场、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学、古典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这些宏伟建筑展现了当时主流自由主义文化的最高价值,这些文化建筑成为了“第二社会”阶层通往贵族的精神阶梯。
另一方面,宏伟的公共建筑建设的经济基础来源于对环城大道上公寓住宅的土地出售的鼓励。环城大道上的公寓市场、建筑、区位分布、类型和风格都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趋势。“个人所有的租赁式府邸在声望和盈利上的巧妙统一,反映出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社会趋势之一: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谐。”(P53)公寓式住宅的外观和内部空间的“贵族化”对于维也纳的各路精英有着巨大的磁力,因此最有名望的建筑师都投身于对租赁式住宅楼的设计:从费斯特尔的英式半独立式住宅到汉森的共管公寓(condominium)。
这些住宅不仅仅是其彰显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最保险、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之一。“无论是财富新贵还是世袭贵族都是19世纪60年代环城大道住宅的重要投资者。”(P54)他们在环城大道上拥有大量的住宅,但真正居住的却集中在明显“卓尔不群”的地带:黑山广场和纺织居住区周边。从小范围的空间分布上,纺织居住区和黑山广场周边具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印记,而宏观上的“环城大道区域却融合了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这两个可变阶层”(P60)
世纪末,对于环城大道的批判虽然是集中在美学上的批评,但是却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态度,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中,文化追求和社会满足之间的关系。其中“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的拟古主义和瓦格纳的功能未来主义,都引发了城市建设上的新的审美观的产生。”西特受到父亲、老师和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响,对以往艺术和传统工艺价值具有无限的热忱。他“忠于手工艺阶层、为其充当教育者、研究者和宣传者,复兴和宣扬其过去的艺术成就,以使其继续存在合法化;他还致力于让相关艺术跟建筑和城市工程建立起联系。”(P71)他作为一个齐格弗里德式的人物,“通过重新设计我们的环境,来重建我们的生活。”(P72)而在他的环境观(《城市建设》、1899年)中,广场成为关键的元素。他用广场对抗街道,试图将城市从孤寂感和对无限空虚的恐慌感中拯救出来。他的公共城市理论后来为刘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所推崇,但在战前的奥地利还未出现普及其思想的土壤。
与西特不同,奥托•瓦格纳设想城市的无限扩张,认为需求和实用性是现代生活的中心。作为现代主义者,他从自身阶级(第二社会)的形象出发来构想城市和建筑。他通过参与城建活动,将技术提升到文化的地位,“把现代生活的需要、现代建筑材料的运用,同艺术需求协调一致起来。”(P82)接着通过参与“分离派”的活动,界定现代人类在建筑中所应表现的人性:“一个主动、高效、理性、时髦的资产阶级——是个时间不多、金钱不少、对具有纪念意义之物情有独钟的城市人。”(P85)唯一缺少的是“方位感”,因此瓦格纳通过强调街道、线条来克服城市人“痛苦的无常感”。最后他通过模块化和理性主义强调了他的城市观:“即设计出来的环境,应该让处于其中的建筑,兼具功能和审美上的潜力。”(P95)
幻想政治——现代群众政治的产物
奥地利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以领导下层进步势力对抗上层落后势力为责任,期望释放群众的政治力量来对抗上层的贵族阶级,却由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本身而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最后在群众政治中,失去了政权。
作者在书中对于政治的讨论,集中在对这一背景下的三位“政治艺术家”的政治转向所体现的社会——心理现实的挖掘。如作者所说,他们“为我们勾勒出一种超越纯政治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模式,构成了开创20世纪、更广义的文化革命。”(P124)
乔治•冯•舍内雷尔以技术型贵族身份起家,本要成为土地绅士的他,领导者那些对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怨恨不已的农民阶层,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了吸纳来自维也纳激进的手工业者,舍内雷尔成为了奥地利历史上最强硬、最彻底的反犹主义者。他进攻性的性格,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政策,也将自己推向了毁灭,同时也引导者它的崇拜者——希特勒将世界推向了悲剧。
卡尔•鲁格与舍内雷尔同样出身于自由主义,同样利用反犹主义来动员全民中的不稳定因素:手工业者和学生,同样利用国会权利以外的政治力量:流氓政治和暴民政治来达到目的,但不同的是鲁格利用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自身的胜利宣告了奥地利古典自由主义统治时代的结束。鲁格由“鲁格博士”起家,通过民主煽动家的才干,跟随者“小人物”的激进立场,“从反腐败到反资本主义,从反资本主义到反犹主义者”。(P141)促使他成功的是不同于舍内雷尔的强硬派,鲁格将反犹主义相对化,仅仅用来攻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联合了足够多的力量:贵族与民主分子、手工业者、与牧师等。
与舍内雷尔和鲁格相比,狄奥多尔•赫茨尔从作家、记者到政治家的路程走的更为曲折,也更为心理化。赫茨尔从对犹太人的反感,梦想成为贵族的资产阶级,到主张社会同化,再到犹太复国的思想变化经历充斥着其个人的挫折和审美失望。在法国的反犹主义和鲁格的胜利的冲击下,赫茨尔走上了领导新的民族迁徙之路。
思想王国——弗洛伊德与弑父情结
“梦是愿望的满足”是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的基本分析原则,也是作者对弗洛伊德的梦的文本与一生的三重危机之间关系的分析原则。职业、政治、个人作为精神考古的三个层面,也成为了作者分析弗洛伊德一生的三个阶段主要途径。其中弗洛伊德在职业上的渴望和自我疑虑是第一个阶段,他通过“叔父之梦”当上部长的政治愿望来解释自己想要成为教授的渴望。而“植物学专论之梦”中父亲的强硬形象将分析带入了第二阶段,在政治上的挫伤和来自父亲的压制在这里成功会师。最后,“革命之梦”将弗洛伊德长期压抑的政治愿望和对父亲的反抗结合表现出来,在无助的父亲取代了图恩伯爵站在月台上时,“弑父取代了弑君,精神分析克服了历史。由于一种反政治的心理学,政治变得中性化起来。”(P203)
作者用《梦的解析》扉页上的文字“假如我无法让权贵低头,那我就搅动起冥河之水。”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本能与社会——心理体验的意义。“精神分析的发现是卓越、孤独、痛苦的,它让弗洛伊德得以克服罗马神经症、跪拜密涅瓦神庙的废墟,并调整自己的学术地位,因此可说是一次反政治的巨大胜利。通过把自己过去和当前的政治问题,简化为有关父子原始冲突的附带现象,弗洛伊德为他的自由派同道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非历史理论,让他们能够承受一个脱离轨道、无法驾驭的政治世界。”(P210)
花园的爆炸——艺术与自由主义自我的危机
从阿达尔伯特•施迪夫特《夏日般的初秋》中唯美主义的理性的乌托邦式的玫瑰屋,到费迪南德•冯•萨尔笔下的挥舞着“红色翅膀”的艺术,再到利奥波德•冯•安德里安的《知识花园》中所构建的激发情感的自我迷恋者的标志,“花园形象”成为了自由主义文化不断变化的象征。在这里,文化与社会结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文化和艺术从充满理性的,有秩序的理想乌托邦,到唯美主义沦为工具的社会阶梯,再到纳西西斯式的自我毁灭,“花园”不断转型。虽有霍夫曼斯塔尔期望将“艺术回归伦理,让审美文化回归社会”的戏剧实践探索,但自由主义自我的危机还是引发了“花园的爆炸”。
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哲学》、《医学》、《法学》三幅天顶画对传统自由主义审美的挑战到柯柯什卡《梦想中的男孩》、《谋杀者、女人的希望》带来的破坏性的直接的启示;从奥托•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修尔特》对传统基调的反叛到阿诺德•勋伯格的《空中花园诗篇》对内心世界和对片段世界所进行的探索,19世纪末最早一批的现代主义者为适应新局面所做的努力被这些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者所代替,“他们同最后的清教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将艺术用作文化粉饰手段、掩饰现实本质的做法。”(P398)在他们的作品中,代表传统直销的花园瓦解了。
结语
休斯克的这本宏著内容详实而不乏味,面相广阔而非纷杂。历史人物的详细论述并未使整部作品脱离从“理性之人”到“心理之人”转变的逻辑主线,反而丰富和巩固了这个转型的所面对的共同的社会体验。
正如作者所计划的,他所采取的各个自主性的分析方法使得每一章都有独特的阅读体验。而在整体阅读的过程中,又能体会到各个分支转变背后的相同的社会政治驱动力。政治的力量成为了每一章都不可回避的话题,虽然有时它在幕后,有时跳到幕前。但这统一的社会体验背景,成为这些人物努力反抗却无法挣脱的宿命。正如文中所述,这一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反复上演。无论是城市建设的风格观念演变、还是美术界的反抗和失落、再或是作为整体语境的心理之人的诞生,都是在对“父辈”的反抗中出现的。
虽是对悲剧的解读,《世纪末的维也纳》却点亮了希望的星火。正如作者所说,对这个时代的研究往往是由于对另一个时代的关注。在世纪末的剧烈变革中,几代维也纳人不断思索着自身的社会的关系,这最初的现代性和心理性的探索带给世界在二战后不同的文化面貌。而同样在世纪初的中国,几代的文人雅士也不断的探索着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留给了当代中国不断回味的思想财富。这两个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世界,是否具有着相通性的“自我重构”的观念变革呢?也许这就是留给新的研究者的思考的问题吧。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八):【读品•细读】章可:维也纳:“现代”的子宫
当谢小盟在重庆上空的缆车里眉飞色舞地说“城市是母体,我们都生活在她的子宫里面”时候,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一个跨越时空的伟大隐喻所附体。从雅典到罗马,从君士坦丁堡到巴黎,那些在历史中闪耀着的伟大城市,无一例外地为同样伟大的创造者们提供了母体和源源不断的养分,任他们在其中遨游,孕育出新的文化生命。百年前的维也纳,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母体,在她的子宫里面,一种被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化正在悄悄地生长。
叙说一个城市,并不是简单的任务,尤其是面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这座哈布斯堡的皇城,和它所代表的国家一样,夹在纸醉金迷的巴黎和雄心勃勃的柏林中间,惶惶然寻求着自我。旧与新,保守与激进,在政治、学术和文化各个领域上演着激烈的争夺。《世纪末的维也纳》的作者休斯克把整个对城市的关注分成七个部分,每部分代表了一个文化单元,分别围绕着如弗洛伊德、施尼茨勒、克利姆特、马勒、勋伯格这些核心人物展开叙述。单独地阅读其中任何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然而,是什么将这些故事连接起来,仅仅因为它们都发生在维也纳这个空间中?显然不止于此。休斯克选取这七个场域,而把诸如哈布斯堡皇室之类的“大叙事”置之一边,乃是因为,它们恰好都见证了“现代”政治文化破茧而出的那一番挣扎。
说到底,什么又是“现代”?二十世纪究竟有什么重要的理由,能够大刀阔斧地把之前所有世纪都划在一边,而宣称自己是“现代”。这其中的深重断裂,或者说转折,究竟在何处?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化多样性是“现代主义”的根本,从没有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这样诞生了如此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作为思想史家的休斯克试图发掘更深,他体察到,在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里,各个学科都不再如之前那样强烈的需要以历史作为自我反省的基础。尤其到了战后,文学研究者们热衷于“新批评”的形式分析,政治学掀起行为主义的热潮,经济学里大行其道的是立足于数学的理论家们,在音乐和美术创作中,新的艺术思维几乎颠覆了以往对历史的关注,更重要的当然是哲学上,如维特根斯坦般哲学史知识贫乏但贡献伟大的人物之出现,赫然成了标志性的事件,分析哲学家们嘴角带着怀疑和不屑,把哲学史讨论了两千年的问题,轻轻地扔到了一边。
在诸如此类的领域里,当学科们大声宣布可以独立于自己的历史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在迅速地消退,学术专业化成了一去不回头的单向街。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绝不仅仅只在学院里萌芽成长,它铺散开来,业已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把多元文化之间仅存的那些纽带也无情地撕断。今天的历史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大一堆碎片,要建立起将它们逐个拼合起来的所谓“通则”,已经变得无比艰难。
用这样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休斯克选择了维也纳作为关注对象。当然,只要是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认为百年前的维也纳已经具有了这种学科的独立和巨大分殊,文化的多元和自说自话。一切都还在孕育之中,有的已经破壳而出,有的却以头破血流的失败来证明历史的反复。但这个城市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缩影,它反映了“现代主义”在萌发阶段,对自己由之诞出的那个传统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这点的刻画贯穿了书的始终,而且毫无疑问它是成功的。
那么,世纪末维也纳的“现代”,针对的是什么?休斯克并没有明确说,他在七个部分里所描述到的探索者们,似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困境,和不同的敌人频频过招。但在我眼里,他们真正面对的,一个是建基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政治”,一个是艺术上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学院里的变革不同,政治和艺术环境,是将要萌发的“现代”文化最直接感受到的,也是休斯克讲到的这些文学、城市规划和造型艺术活动家们所共有的社会体验。世纪末的维也纳,“自由主义”的政治运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压抑和失望弥漫于政治生活之中,非理性的甚至幻想性的政治情绪开始滋长;另一方面,对现实的失望却导致了公民们艺术需求的膨胀,一种焦虑、敏感的审美文化开始蔓延,随之而来的是艺术的古典形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背叛,人们不断地追求新的个人色彩和主观风格。
休斯克的维也纳之旅开始于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但他对这两个德语文学的殿堂级人物并没有着墨太多,在书中只相当于一个小引,以两位大家的创作来折射集体的政治心理和艺术趋向。其后精彩的部分是关于维也纳环城大道的,城市规划是最能反映政治和艺术双重角力的主题,十九世纪中期建立起来的,作为“自由主义政治”之象征的环城大道格局,在世纪末成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批评的焦点。以西特和奥托•瓦格纳为代表的设计师,在重新塑造维也纳城市风格的同时,也提出了独特的城市形式理念,启发了后来诸如芒福德等“现代”的理论家们。
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催生的产物,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针锋相对,是世纪末的维也纳政治生活里最突出的一面,休斯克对相关的三位政治领袖的描绘尽管细致,但不免显得有些沉闷。同样涉及反犹这个主题的,是另一个焦虑的人物——弗洛伊德,作者把目光集中在弗写作《梦的解析》一书的前后,将他在学院中的政治困境、成长经历里酿出的“弑父”情结,与《梦的解析》这个文本作了有趣的比对,把一段曲折的个人历史,和一种普遍的梦境分析原则巧妙地联系了起来。
在这些平稳冷静的叙述之后,《世纪末的维也纳》终于迎来了它最为辉煌华丽的最后三章,这些篇章属于克利姆特和分离画派,属于徜徉在花园里的诗人们,属于柯柯什卡和勋伯格。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富有感受力,最具原创热情的艺术家,也是那个时代焦虑善感的审美文化的最好表征。当分离运动的画家们选择了“给时代以它的艺术,给艺术以它的自由”作为口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自觉的统一创作路线,他们只是受压于呆板的学院古典空气,而急迫地追求个体的“自由”,这种自由帮助他们直接地与心目中的美,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发生印合。当作曲家勋伯格画出那幅《红色凝视》的时候,他把握到了童年柯柯什卡躺在垃圾堆里时那种痛苦的生理体验,这种体验在不经意间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它带着乖张、叛逆、焦虑的神情审视那个“必然”的强大的现实秩序和心理秩序,用一双血红的眼睛寻找个体的艺术空间。
去年春天,克利姆特的一幅《阿黛乐•布洛赫-鲍尔夫人》拍出了1.35亿美元的油画拍卖天价,把原纪录保有者毕加索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幅熠熠生辉的肖像画属于克利姆特晚期“黄金风格”中的代表作,在人物平静而略带病态的外表下,这位一生在“战斗-受伤-逃避”中不断轮回的伟大画家,终于又重返了早年的典雅和从容。一百年来眼花缭乱地吞噬着人们心灵的“现代”,终于以这样一种最具标志性的,疯狂的物质方式回归到了它的原点——世纪末的维也纳,回归到了身着华贵服饰的犹太富商夫人面前。
《世纪末的维也纳》读后感(九):卡尔•休斯克与《世纪末的维也纳》
“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生于纽约市,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为代顿-斯托克顿历史学教授,并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欧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休斯克曾在卫斯理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担任教职。他还是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会的成员,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1917》(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10-1917)、《德国问题》(The Problem of Germany)、《以历史来思考》(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转变中的美国学术文化》(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 Fifty Years, Four Disciplines)等书。《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是其代表作之一。” 大卫•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曾评价本书:“堪称当今一位真正原创性学者的跨时代著作: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政治分裂、社会瓦解,但众多现代艺术与思想却从这种危机中诞生,而本书正是对此所做的精彩揭示。该书不仅对早期现代主义在政治环境下的诸多方面做了精彩的探索,更体现出最具才干与雄心的巨匠研究思想史这门学科所用的方法,同时面对现代主义有关历史早已过时的轻蔑所指,对史学自身做出了有力维护。”
然而,要理解这些对该书的赞誉,首先就要理解为什么休斯克会这样选题。换句话说,就是“世纪末”的维也纳,为什么是19世纪末的维也纳,而非奥斯曼土耳其人包围维也纳时的维也纳,或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维也纳;为什么是世纪末的“维也纳”,而非世纪末的伦敦或者巴黎。这个问题可远非休斯克是奥地利的研究专家这么简单。如果从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该书远非成功。有学者曾一度对该书表示失望,“该书明显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部七篇文章的杂烩”。 “休斯克的书不像威廉•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的《奥地利精神》(The Austrian Mind)一样,对世纪末的奥地利文化的所有领域作充分揭示;也不像雅尼克(Janick)与图尔明(Toulmin)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一样,明确探求世纪末的维也纳与我们自己的时代有特别联系的原因。然而,当读者放下休斯克的书时,他一定会思考该书字面意思之外的内容。” 《世纪末的维也纳》所讲述的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内容,并不具有独创性。可见,讨论《世纪末的维也纳》,如果只讨论该书所讲述的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的内容的话,与讨论其他相关书籍相比,并不具有新颖性,也不符合休斯克的设想。但就该书讲述的内容而言,并不能撑起对该书的高度评价。
实际上,该书并没有尝试去总结世纪末的维也纳的精神,休斯克也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认为,“史学家当前必须放弃的,特别在面对现代性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是预先假定一个抽象的和绝对的通用标准,即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和密尔所说的‘时代特征’”。 即使休斯克天赋秉异,他也并没有打算让这本书成为讨论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的“决定性”(definitive)的作品。有学者很欣赏休斯克的这种做法,认为“尽管有大量的史料,但高质量的作品是很少的,而约翰斯顿在《奥地利精神》中尝试概括该时期奥地利的文化发展,除了一些吸引眼球的言论之外,就只剩概括而已”。 所以说,讨论该书时,不应该只关注休斯克所讨论的问题本身,还应该注意休斯克为何要关注这些问题,即他的关怀是什么,以及他是用什么手段来回应这种关怀的。因为休斯克明白,就现阶段而言,尝试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精神作宏观概括并不明智,而他的作品若只是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精神作叙述的话,他并不一定能够比更精通于此项的同行做得更好。所以,该书看起来并不像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连贯的概括,而是看似零散而并不面面俱到的文章的集合。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休斯克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的叙述并不一定能够比得上其他同行一样的细致与面面俱到,那他选题的目的在哪里。然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令人困扰。因为类似“为什么”这类的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答案,我们无从得知休斯克内心的真正想法。总是要揪住学者在写作一部作品的时代背景的做法也令人厌烦,因为时代背景这种东西如何作用于个人写作上,也让人捉摸不定,而休斯克本人也反对讨论所谓的“时代精神”。然而,即使百般不愿,笔者讨论该书也还是绕不过这个话题。首先,就该书论述的内容而言,并不比其他相关的作品更新颖或者是使用了新的史料,却获得了高度评价,这之间并不平衡;另外,休斯克本人在书中也谈到了他创作该书的时代背景,这似乎也不应该忽视。总之,尽管无从得知休斯克心里想的实在是什么,但笔者打算分析休斯克至少在文本上表达的关怀是什么,以及他在文本上是如何实现他的这种关怀的。
休斯克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到,“现代人已然对历史漠不关心,尽管历史曾被视作连续提供滋养的传统,现如今早已无甚价值”,“然而对于历史之死的认识,精神分析学家也绝不可以忽视——在最明显的层面上,他们至少可以把这种决然斩断与过去的维系,看成是一代代人对其父辈的反抗,以及对自我界定的探求”。 在休斯克的这段话中,涉及到两个主题——一是写作的时代背景:“历史之死”;二是为何要选择世纪末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
“历史之死”究竟是怎样一个创作背景呢?有学者指出,“二战后,美国的政治与学院文化出现了深刻的变迁。大战几乎摧毁了自由主义的信心,进步与理性遭到全面怀疑,学院里的各个专业,从艺术到经济,一个接一个地切断自己和历史的联系,纷纷转向理论自足以及自我指向的分析批评,原来从公众与社会领域来研究人类苦难的做法,也逐渐转变成从私人和心理领域入手。‘去政治化’倾向与‘去历史化’潮流结伴而来,构成了20世纪‘现代’文化的独特景观”。“休斯克将他的目光聚焦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希望透过这个‘预演大戏的小舞台’,来呈现一幅破碎历史中的清晰图景,作为同样是破碎的片段化的战后美国现实处境的一种文化寻根。”“在他看来,世纪末的维也纳,许多新文化的创作者是在进行一种集体的伊底帕斯式(Oedipal)的反抗,反抗培育他们成长的古典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世纪末’的文化特质,在这里被大致界定为‘断裂’。”
休斯克创作该书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50到70年代,而这个时期,历史学作为知识的模范或者是艺术革新的源泉的价值受到了新的挑战。美国哲学家讨论历史学的价值,讨论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曾指出,如果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它必须要拥有一些规范。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理解的自主性”(autonom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知识,而只是一种写作。甚至历史分析哲学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但分析哲学并不是对人文或理性历史造成最大影响的。法国的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在“理论”(theory)的框架下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这使得语言学、人类学都从历史学中撤退。 对历史批评最著名的攻击来自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认为,历史叙述虽然没什么坏处,但并不能将其看作一种知识,它只是一种文本,一种书写。法国的情况也影响到了美国。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此有所回应。他提出了“历史的修辞”(rhetorics of history),他反对历史作为判断的中立的基础,认为历史书写创造了真实的标准,根据历史学,它们本身无法受到判断。
以上只是对休斯克在写作本书时遇到的学术背景所作的一个简单的概括,实际情况要远比这个复杂得多。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涉及了大量的人物与术语,每一个术语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通的。于是,为了能够使讨论继续进行下去,笔者放弃纠缠此类术语,而对休斯克所遭遇的境遇作更精炼的概述。简单来说,休斯克在写作该书的时候,历史学的地位遭到了“去历史化”潮流的冲击,休斯克打算通过说明实际上“去历史化”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来捍卫历史学的地位。于是,“去历史化”就对应了休斯克所谈到的“历史之死”,而对“去历史化”潮流给历史学界带来的冲击感到担忧则构成了休斯克写作该书的关怀。
至于为了回应“去历史化”潮流,休斯克为什么要选择“世纪末的维也纳”,上文有提到休斯克试图为“去历史化”寻根。休斯克看到,奥地利“到了世纪末,尤其是最后的五年,‘空气中弥漫着对于社会与政治将形解体的震颤’,自由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发生了重大危机”。 休斯克感到,“世纪末的维也纳”与“去历史化”的美国学术界有相似之处,都是自由主义信心丧失,都是进步与理性遭到怀疑,为“世纪末的维也纳”寻根,即是为“去历史化”寻找历史之根。至于休斯克为什么谈到“历史之死”不可以忽视“精神分析学家”,笔者打算在该书的文本寻找其如何回应序言,在后文讨论。
既然休斯克打算回应“去历史化”,该书又是如何表现他的这种回应的呢?让我们在书中尝试寻找出一些端倪,先按时间序列理清该书所叙述的故事,将休斯克零散的几篇文章连贯起来。
“1860年,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分子在哈布斯堡帝国西部,迈出了他们执掌政权的第一大步,并且依照立宪的原则和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改造了国家机构。”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掌权之后,在与军方经历了一番争夺之后,获得了皇宫与平民区之间的一大块空地,开始修建属于他们的“环城大道”。“由于其风格统一、规模宏大,‘维也纳环城大道’已经变成了奥地利人的精神概念,能够在他们心中唤起一个时代的特征,就仿佛‘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之于英国人,‘创建时期’(Gründerzeit)之于德国人,或者‘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之于法国人一样。” “支配者环城大道的,不是实用,而是文化的自我投射。” “它们就像风向图一样,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议会政府在国会大厦里,市政当局在市政厅里,高等教育在大学里,而戏剧艺术在皇家剧场里。” 自由主义建筑师西特“试图扩展历史主义,把人类从现代科技和功利当中拯救出来”。 他认为,“一座城市,其建造方式必须要让市民立即就感觉安全与幸福。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城市建设就决不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毕竟,“使得自由主义者掌握权力的,并非他们自身内在的力量,而是由于旧秩序败在了外国敌对势力的手中”。 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联手率领皮埃蒙特人与法国人先后在伦巴第与威尼西亚取得胜利,以及俾斯麦率领普鲁士人在波西米亚取得胜利,使得自由主义者在与军方的争夺中占据上风。然而,自由主义者再也不能再现20多年前的那场将梅特涅赶出维也纳的革命中领导大众的场景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自由派分子制定的反对上层阶级的计划,反倒引起了下层阶级的爆发。自由派分子们成功地将群众的政治能量释放出来,可是矛头对准的却是自己,而不是他们的老对手。针对上层的敌人放的每一枪,都会在下层引起一阵充满敌意的乱枪齐射。” “新生的反自由主义群众运动——捷克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于下层,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托管权力、破坏其政治制度、削弱他们对于理性历史结构的信心。” 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者“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价值,可他们在维持议会权力时,依旧采取了限制公民权这种不民主的举措”。 但是,自由主义最终还是回天乏术,“即使在全国层面上,自由主义者作为一股议会政治力量,也在1900年之前即被破坏,以致永不翻身。他们已经被现代群众运动、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彻底击垮”。 反自由主义者瓦格纳“想要压制历史主义,来迎合一贯理性的城市文明价值观”。他“在其规划中,就把维也纳设计成一个庞大的都市,并且还配上一句让卡米洛•西特听了定会心寒胆颤的格言:‘需要才是艺术唯一的伴侣(Artis sola domina necessitas)。’对于这个阶段的瓦格纳而言,‘需要’就是指效率和经济上的需求,以及为商业追求提供便利”。
“自由主义垮台这一巨大灾难,进一步将美学传统转化成了一种敏感不安、崇尚享乐、极度焦虑的文化。而奥地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摒弃他们的早期传统,即法律中的道德和科学文化,又使这情形更加的复杂。因此,在奥地利的高雅文化类型中,对艺术和感官生活的肯定中间,却夹杂着负疚感。” “在维也纳,偏偏正是政治挫败感,才促成人们发现了这一如今无所不在的心理之人。”“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聚焦于理性的人(rational man),他们相信,只有这种人才能凭借科学驾驭自然、凭借道德约束自我,从而创造出美好社会。到了我们这个世纪,理性的人不得不让位于内涵更丰富,但也更加危险和易变的生命,即心理之人(psychological man)。这种新概念的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具有情感与本能的生命。我们也倾向于将他作为文化中各个方面的衡量尺度。”
此时,精神分析学家的角色出现了。“从家庭环境、个人信仰、种族关系来看,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都属于最受新势力威胁的群体:即维也纳的自由派犹太人。” “休斯克展现了弗洛伊德‘毕生与奥国社会政治现实的长期斗争’。” 自由主义的失败使得弗洛伊德“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满怀怨恨的处境”,而这种处境“牢牢支配着他醒时的幻想”。 “他所做的梦以及对这些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他因父亲之死而产生的心理危机,实则是出于职场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内疚。” “通过把政治问题转化到个人的心理范畴中,他重建了个人秩序,而非社会秩序。”
通过对该书时间序列的梳理,我们明白了休斯克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回应“去历史化”的——政治史。自由主义在奥地利的失败这一政治史贯穿了全书。正是自由主义的失败才导致“世纪末的维也纳”逃离政治的现象,人们从关注“理性的人”转为注目于“心理的人”,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正是逃离政治的反映。自由主义者扩张历史主义,自由主义失败之后,人们对其感到失望,于是便斩断与自由主义的父辈的历史联系,压制历史主义,因而呈现出一幅“无历史”的场景。
可见,休斯克的几篇文章并不是无意义的杂烩,而是一部连贯的政治史。休斯克反击“去历史化”的伙伴,正是与“去历史化”潮流一道而来的“去政治化”所针对的对象:政治。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所寻求的,是‘把政治与文化统一在主旨中,把历史与形式分析统一在方法中’”。 “在‘世纪末’的共时图景中,政治与文化互为环境,互相影响,这是本书七个章节‘并置’所产生的效果,正好指向作者所要探讨的主题:政治与文化的互动。”
在该书中,“休斯克是想暗示:所有这一切对历史的否定,其实都不过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以一种与前一代人不同的方式确定自身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换句话说,这种反历史的态度,与之前对历史的狂热态度一样,都是在回应历史”。 休斯克“努力在‘历史女神’衰落的图景中发掘着现代面孔背后的传统因素”。“《世纪末的维也纳》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细致地呈现了一种‘无历史文化’的酝酿及其诞生过程,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表达着对当时所处文化潮流的方法论反拨”。 休斯克“藉由以这一历史化了的潜意识范畴和加入了社会与文化维度的精神分析方法去解析这个时代,在历史的外壳中又加入了这个时代的反历史的特质。” 于是,“‘世纪末的维也纳’,成了一面‘文化之境’,在休斯克对这一‘断裂’历史的感同身受似的描绘中,隐约浮动着20世纪以拒斥过去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的影子。然而,既然宣称自己完全独立于过去的‘现代文化’,在19世纪末的奥国找得到深刻的历史根源,那么所谓的‘独立’并非绝对,所谓‘现代’,也不等于‘无历史’:休斯克所创造的这个历史镜像,一面缓释着现代人‘无根’的恐惧,一面却在不意间揭示了‘现代’与‘历史’的吊诡”。
上一段所引用的学者的论述可能并不够直白。简单概括上述观点,也就是说,休斯克回应“去历史化”的工具是政治史,他在该书中,阐述了奥地利在19世纪末自由主义失败的政治历程,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历史主义的压制。同时,休斯克在该书中回应“去历史化”的手段是为“去历史化”添加历史的外衣,通过指出世纪末的维也纳压制历史主义是由自由主义失败这一政治史所导致的,来暗示当时学术界“去历史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应,以此来捍卫历史学的地位。
总之,在该书的文本中,可以瞥见休斯克很明显地是在回应“去历史化”的潮流。而他思考“去历史化”这一问题后的回答,则是为“去历史化”罩上一层历史的外衣,让一切又回归历史。这或许就是让读者“思考该书字面意思之外的内容”,也使得该书虽然没有对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叙述,却依然获得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