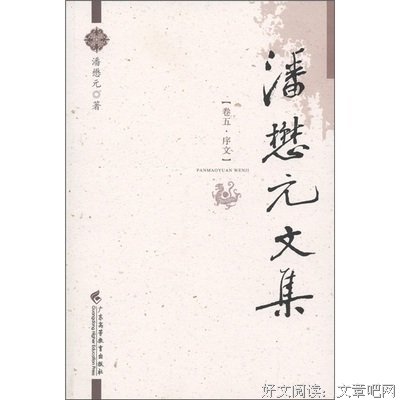《马雁诗集》是一本由马雁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雁诗集》读后感(一):自白
自白
为什么要写诗
为什么要死
你一问我便理屈词穷
可你写诗
你死
不费吹灰之力
这不是一次谋杀
因为你不停地说是的
你必死,因为死亡
对于女人来说是最大的
胜过男人的
你说:“亲爱的,我正死去”
我没法开口阻止
因为被你坐在臀下
不能开口
也不能变形
像我这样的过山车
思考着诗与死亡
载着世上漂泊的女人
在同一根钢轨上
磨耗着胶皮
《马雁诗集》读后感(二):亲爱的,我正死去……
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之后,断断续续找到许多诗。这个没有诗的年代里,读诗,是一种奢侈。
读诗,是一种死亡。
抄写一遍你的诗,念你:
亲爱的,在成都,雨雪开始于清晨,
我正死去。我在阴沉的下午死去,
你看,自从那时起,我就混乱至今。
我们都有节日,你穿过锋利的北京,
亲爱的,穿过高大的白杨树,他
一个声音就处死了你。谁也不能
处死我,你的尸体叫我快活。你我
对,我无耻近于勇,请亲吻我吧,
与死亡有关,与一切的堕落有关。
《马雁诗集》读后感(三):打个饱嗝淋成狗来读马雁
从图书馆挑拣出一本《索列斯库诗选》
好吧
至少汉字还串联着我们
至少新加坡汉语者还能叫“华侨”
还有嫣红的迷人之食
似乎是琴瑟相合的开场白
偏执让我为每一首“为XXX而作”构思一个故事
要拟合年份与季节
要捕捉彼时我还是稚儿的惶恐与狂妄
我没有偷看,你主动抽丝剥茧
你无畏衣带渐宽、赤身裸体
水、水、水
还需要快递
无处不在的二氧化氢
此刻还降落在窗外的海岸上,模糊了
对面无人居住的岛屿夜色
我的手指翻着你的诗集
我的舌头品尝着牙龈出血的腥
没有甜、没有甜
裹尸布才不是三分之一个宇宙弦
我贪生恶死
追着我的后摇扫过时间轴
这本不相干的夜晚与繁星
还有那
狗屁膏药在你豆瓣诗集界面下的丰、胸、广、告
《马雁诗集》读后感(四):請借我幻覺之舟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亦是在馬雁暴戾地自死后,如那群被腐朽、腐爛氣息疾速吸引的屍蛛的其中之一,在無敵、孤獨的死亡面前垂下小小的眼珠,再吐以多餘的蛛絲妄圖包裹那些無力的詞句,屍體卻像深秋墜地的落葉,歸家返鄉似的緩慢溶解在泥土中。這種令人絕望的緩慢,絕非停留在死者身上,而是時間以其無言的方式腐蝕生者。我現且安靜地坐著,寫些什麽給她,約莫就像當年雙手冰涼反復翻讀紀德,在冬夏反復交替的窘迫歲月里,寫幾封永遠寄不出的信給馬驊的她。但作為生者的我仍舊承受著生命的重複與輾轉、傾斜與延宕,她卻停留在沒有止境的無限延續里,不再書寫綺麗萬里的幻覺與痛苦,也不再有詩歌隨著塬上的男神穿過她的身體。
第一次讀馬雁,是那首《在小山上看湖》。夜晚平靜疏朗,路燈與公路遙相映襯,四人緘默少言,聽機械的打樁聲音。湖面那麼小,區區一畝而已,四個人竟能看得如此長久。結局是有力的:“我們像情人一樣沉默,像看情人一樣看湖。”兩句精准地表述出曖昧而沉寂的狀態,節制而孤獨。我訝異于她述物記人時的平實,畫面感十足,還有那信手拈來的秩序與韻律,對氣氛熟稔的把握,那時我便知,她絕非池中之物。之後又慢慢讀了當時她發表在網上的其他詩歌,當時我輕率地認為她是個苦行者,運用節制而被壓縮的技藝,如赤足行于熔岩之上那般寫作。無論是《北中國》中盛大的氣象與渺渺世俗由寬闊至狹小的對比,還是《我們乘坐過山車飛向未來》先賢智者授以痛苦的智慧之路,無不表現出的是她憫人的贖世情節,她是世間苦痛的承受者,并借此修行成為更加成熟、堅定的傳道者。
但我錯了,之後在書中讀到她早年的詩作,那之中展現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馬雁。在後期詩作中逐漸消失隱沒的女性化特徵,卻在她早期的作品中異常明顯。我相信那其中絕對有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聲音,《晚上,日光燈照著這些人》尤甚,如一首跛足或斷頸的仿作,但馬雁與普拉斯絕不相同:在《迷人之食》中,她的女性化更多顯現為少女式的;而且她不像前者自棄得潑厲決絕、歇斯底裡,更多的是處於成熟與青稚之間的清明與潔淨,甚至帶著些許惶恐與驕矜。她描寫做愛后,躲在她懷裡脆弱如同一根頭髮般的情人,或是近似于同性戀人般的女友之間的嬉笑,慾望的笑靨與嗓音。但她寫的更多的是甜膩魅惑的死亡。她相信她必死(並且,她確實以她自己的方式做到了),她相信,死亡是最大的政治——誰又說不是呢?
不同于後期詩歌中的節制與遼闊,早期作品中顯現出的是抒情化的傾向,而且詩歌在古代追憶、憑弔與饋贈的功能,她使用頻繁,且樂此不疲將自身的幻覺糅合其中。比如在《櫻桃》中悼念的,被異化為痛苦、空無的母親,以及被異化成病變患者的馬雁本人。(無法不想起張棗絕妙的“上午,仿佛有一種櫻桃之遠”,而櫻桃在這卻被馬雁描述得如同禁果般妖豔、甜腥),在《親愛的,我正死去》里,陰霾的雨雪中,她面對她那與她一道,“曾經是英雄的小姐妹,但現在是灰暗的中國大地上墮落的一對”的女友,竟大聲地宣佈:“對,我知恥近乎勇。”她坦誠她的陰暗,急死之熱切,她幻想兩人之死,那如判詞的“我正在死去……”異常懾人奇詭,如入死亡庭院一探死者狂歡的奇景。還有題記為獻給Emma的《我們的道路》中她的波西米亞情節,似乎能一睹她看著友人攜著皮鞋上揮之不去的污垢遠行而去,她揚起長裙,跳一支陳舊的舞蹈,轉圈,顛步,脖子上的鈴鐺叮噹作響…
我不知道,如果她不依循幻覺的節奏寫詩,而是…啊,我完全無法想像她生命別的可能性,她已然完成了她作為詩人的一切,不論之後生命會帶來沉痛或是甘美,她卻已經提前終止了一切。但我有理由相信,如果,只是說如果,她能夠堅持她苦修者的身份,不拒絕更多痛苦的可能性,她絕對可以成為更加一流的詩人。話說到這兒,卻又像苛責了她自己選擇截斷的生命,可此刻我胸中亦只有冰涼的虛空,怎能空言應該不應該,如何不如何,如果不如果。但作為一個無才華者,確實還是有資格坐上她那支搖搖曳曳的幻覺之舟,體驗一回幻覺的溫柔與殘酷的吧,即使今夜渡不過這冥河之水,餘生浩渺,停下應也是個好選擇吧。
《马雁诗集》读后感(五):无题
看到岑灿说,城市里面就像马雁说的“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觉得很荒凉。想起来一个词叫爱莫能助。关于生活,关于死,关于现在,说得太少。这是活着的人的无能。半夜起来写了一首。马雁,好,干净纯粹。读读《冬天的信》就知道。
《马雁诗集》读后感(六):悼马雁——
1.
公允地评价一位饱受抑郁症折磨的诗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她的诗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与病症纠缠不清的句子,一些与诗的距离较远的句子。“每背叛一次,就有一粒毒药/顺着喉管滑到岩石底部。”而这,作为一位评论家,是无可指摘的。
这本由冷霜老师编选的诗集,不可谓不好。马雁的杰出诗艺一目了然。但我想到的是其中的一首诗,P96《世界下着一夜的雨……》。
2.
这首诗其实有两个版本。马雁发在豆瓣网“写诗”小组里,第一稿和第二稿前后相隔五天。且在同一个帖子里。第一稿诚然写得不错,然而第二稿真正达到了一种完美。
下面是我对第二稿的赏析——
2007-12-14
世界下着一夜的雨……
(为早夭者某)
世界下着一夜的雨,
这寻常一夜——
有人在酒杯里沉没、浮起,
这些并不仅仅是概念,
你会同意,世界必须归类。
我想着,仲春天气,园中的乔木,
水草,以及人在岸边舞蹈。
我们享受过的朗姆酒冰淇淋……
呈现给你,也许就有变数。
但也许不,他人的愈合与你无关。
我迟疑在那个仲春,
早晨的口红,照相机。
中关村。与爱过的人一起吃午饭。
犹太史。闷热的咖啡厅。
唯一的一个晚上:
你爬山归来,刚刚度过一场危机。
我愿意你脸上一抹红晕……
像坟上一圈小小的白花,
像一个软弱的慰藉。
但宁可这样打住。
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坚信:
那一刻我与你同在。
那一夜的雨也淋湿我。
你意味着不敢想象,
但未必不祥。
此刻我只能缅怀那只温暖的我握过的手。
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对记忆的镌刻。
马雁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诗人。相信我的断言。在这首诗歌鉴赏中我将为你证明。
首先,请先注意下这首诗的题目设计:“世界下着一夜的雨……”注意!不是“下了”(过去时),而是“下着”(现在进行时),有一种凝然的感情基调,表示一种状态。世界下着雨。什么?怎样?如果是“世界下了一夜的雨……”那么这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话式的,浪漫主义气味的,“大众”标题。而世界下着一夜的雨却很醒目,它独特,要求你注视。括号内是为早夭者某的提示。第三行开始连续三行并排出现的“有人”开头,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下雨,所以只能进行室内活动。接着是介绍——
我建议看到这里的读者能够有耐性的多读两三遍全诗再回到这一句。有益二字其实暗含着作者对死者行为的一种淡淡的否定口吻,消磨则“很安全”,很不着痕迹的否定——对,还是否定。是趋向自我毁灭(耗损)的淡淡否定。“沉没,浮起”这两个连续动作也暗示了一种死的气息,一种无意义的气息(“下降,上升,下降”),但显然——这也是“安全”的。但也属堕落。通观三句,似乎只有第三种人的行为作者的态度立场是不置可否的。捏碎懦弱(好吧?),锻造自我(积极的),但如果联系前两行你会发现三者有个共同的色彩基调:就是“安全”。捏碎(指向内,而不是向外),而锻字的金字旁有火炉锻造的热量,恰与电视机前的“较静”,与酒的“水气”对比,有令人莞尔的小心思。第七行首次出现“你”,艾略特曾经指出诗歌中存在三种声音,三种不同的对话。而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我想着,仲春天气……”由之前的夜景切至春光明媚,鸟儿啁啾的视野,而“我们享受过的朗姆酒冰淇淋……”则出现的比较突兀。——这是初读这首诗的读者比较困惑的,这还算好诗吗?我的解决方法是多看。再多看四五遍,我发觉这里是别有用心的。这里仿佛切进的一小段酒吧回忆——就象电影,某些文艺电影爱做的那样。而这种对回忆的推出方式必须是比较凝重的事件……这是两个空间的第一次平行结构。“如果把生活中的伤痛呈现给你……”这里已经很显然了,这是对死者的呢喃与自言自语。下面将出现全诗最高超技巧的两句:“我迟疑在那个仲春,温暖而黑暗的聚会……”不要小看“迟疑”二字,笔者曾经在介绍张枣时说过的“汉字本身的诗意”这里出现了:“迟”,对应于死者已去的现在,因此迟疑这个词是无可替代的!而这里上下两句有了一种化学反应般扭曲交缠在一起的空间坍缩感,充当诗中叙述者的“我”此时身在何处?在仲春的河岸边还是黑暗的午夜聚会上觥筹交错?一个伟大的空间折叠方式。
聚会,必然是温暖的,然而黑暗一词可以看出马雁作为优秀诗人的语言禀赋了,一石二鸟:既说明了时间:夜晚,又暗示了聚会时的“小小不正常感”。啤酒,拥抱,早晨的口红,照相机。要解说这里还要再次请读者们多读读全诗——而我的一个理解是,这可能是“我”(女性)与死者(他)的初次相识与发生关系。插一句说,这里的意识流手法十分娴熟而漂亮。“拥抱,早晨的口红,照相机”这是可能性较大的一种解释。中关村,意识流撤远,到一个孤岛。“与爱过的人一起吃午饭”。问题又出现了,而且问题来的很大。如果我们前面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里的可能“我”与“爱过的”人一起吃午饭。就说明他俩关系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了。有必要进一段作者的写作年份生平,考虑到写作时为28岁的女性,那么有可能的,那个“温暖而黑暗的聚会”是两个昔日恋人的重逢。对,没错,应该是这样。那么“如果把生活中的伤痛呈现给你,也许就有变数。”的亲密语气就完全成立了。意识流手法还有最后一句:“犹太史。闷热的咖啡厅。”作者究竟要说什么呢?犹太史,大家应该知道,是一部苦难的历史。——于是答案出现:死者(他)在吃饭时由于昔日恋人关系,说话就失了分寸,把这么沉重的话题(男的一向很迟钝)拿到喝咖啡(这么轻松的环境下聊),于是才会有“闷”,“热”的咖啡厅。“全部的生活细节正在涨潮……”注意,“涨潮”暗示了叙述者我又站临水岸了,那仲春风光无限好的水岸。一石二鸟法则。(非花非雾)
下面是本诗的第二个大问题:“唯一的一个晚上”:让我果断地判定他们俩是离异夫妻吧!(强调,是诗歌中的“我”和“他”)因此才会有“全部的生活细节”,但怎么可能是只有“一个晚上”!?所以说这里是一个象征手法,表示死者“不正常一面”的全面暴露:
“你爬山归来,刚刚度过一场危机。”应该说诗歌直到这里,才第二次明显地断言了“他”的黑暗内心境况——(这需要多么克制,多么高超的技艺才能做到!)“我愿意你脸上一抹红晕……”注意这里有省略(暂且不表),与紧接着的下一句“像坟上一圈小小的白花”多么惊心动魄的意象!但问题是“红晕”和“白花”像在哪里?我觉得是美。美丽的意思。
好了,倒回来说红晕那句。为什么会有红晕?有人说是累的,那太不靠谱了,如此密实严谨的作品中不会允许松散的意象存在的。应该是羞涩。因为觉得晚上出远门(爬山)太不“正常”了,对于开门的“她”(我)不知作何解释——又能做何种解释!如果对人已经没有爱与善意,是不会害羞不好意思的。——像一个软弱的慰藉(美丽,与爱意),更确切说——善意,在这里太过无力了。于事无补。这是千斤重的艰困生活。“他”已无路可逃。“但宁可这样打住。”留意但、宁可这样的词,说明“我”在最后对死者(自戕?)的行为评价是矛盾的。矛盾异常。——不要怜悯,拒绝怜悯!!(马雁无意中预言了自己的结局)……而这样的句子“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多像壮士断腕的暴烈!“那一夜的雨也淋湿我。”诗文行进至此,相当于在叙述者之外,在时空之中,又混入了一个梦幻之夜,一个虚空中抖落的雨夜,这里,此雨夜究竟是彼雨夜还是其它,已经不再重要。类似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不禁让人联想起策兰,这位德国当代最伟大诗人的后期诗作痕迹。(同样是犹太人关键词的惊人“巧合”!)“乡村上空”暗示“我”现在身处墓地,如若联系前文“园中乔木”……则是十分意味深长的延伸。
“但未必不详。”我的理解是,死亡让死者永恒了(只要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朽?……)最后提到的一点是结尾的处理。最后一行“而我此生的工作”工作二字把人的心境拉回现实中的常态。慢慢褪掉抒情的沉郁。通观全篇,一句话:堪称大手笔。
3.
仅以一首诗来盖棺定论一个诗人确实有些武断。但不要忘了庞德曾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写出大量惊为天人的作品。作为一首长诗,她技巧的纯熟,她叙述的克制,她超脱的眼光……无一不是大诗人的特征!至于另外一首,我在网上听过的视频朗诵《学着逢场作戏》就更是大诗人秉性的自然流露了。
谨以此文悼念此刻远在天堂的马雁。
2016.8.7李因
《马雁诗集》读后感(七):马雁你好
我是去年春天知道马雁的,那时,马雁的诗歌散文集出版。于是我不得不再一次感叹,诗人死之时,便是我们生之日。我们活着的这个时代或者稍早的时代,有一大批精英在从事着艺术或思想创作,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直到她/他英年早逝,我们在心里长啸一声,在夜里向空中抛洒一团招魂或致敬的鲜花,生命得到一次新的鼓励和升华。
古人说,人者天地之心。与精英同一时代,尤其能感受到这颗心。然而即便同是精英,也会因时势造化、禀赋气质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马雁去世于2010年的冬天,那一年春天,中国诗坛上另一位诗人张枣去世了。大约也因此可以说,张枣属于春天,马雁是属于冬天的。
读这本马雁诗集,跨越了这个春天的三月——耽搁了十多天,现在才抽出空闲写点东西,其实当初没打算写什么。每天我出门,一般是去图书馆,在打开学术类书籍之前,我都要读一会儿马雁的诗,有时候时间一长,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三月实在是最美好的春天月份,毕竟江南三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洵可信。在读诗的过程中,除了诗篇的涵义,我特别注意每首诗的写作时间,同时注意马雁的生平事件及其与诗篇的照应。
马雁是成都人,回族人,又是北大才女,这些都构成了她极其鲜明的标志,让我能更加深刻而清晰地辨认她。散文集里有《我在中文系的日子》,看来“北大才女”注定要成为近现代中国大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长廊。而马雁是多么地不幸。我倒不是说她的早逝,而是说其实她活得一直都很平凡,她甚至有几次在诗里直言“我没有钱”,我由此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调生命的马雁。然而诗人迪兰托马斯说过,美丽的心灵到处都有见证人。马雁和张枣都能证实这一点。马雁很多诗的副题都写“给某某”,这类诗的比例之高当世少有(于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当下熟悉的名字)。大约高贵的心灵总是特别渴望寻求惺惺相惜的知音,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的那种旷古孤独感所引起的痛苦,只要看到吾道不孤,活着总要容易一些,快乐尽管微小,却足以让人得到安慰,继续自己的生命事业,不至于枯萎。
我认为,当代诗的一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生命存在。要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断言“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就在当代”,恐怕没有人可以驳倒我。因为作为发言者,我在同时代的人身上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共振。我们不必费尽心思排除各种复杂的干扰,而是直接感受到那些杰作的真实和可贵。至少,这可以算作马雁当世意义的一种。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马雁就是“最伟大的诗人”,其实马雁的诗多是对生命和生活的直觉感悟,是非常质朴的。以她犀利敏锐的才气,尚且自谦道“只接触到了诗歌最浅表的一层”和“我所具备的能力仍旧非常有限”(《无力的成就》),我们就可以平和地面对任何狂妄喧嚣和自大了。
以我判断,马雁和许多诗人一样,属于早慧的一类人。早慧有早慧的坏处,可能那份生命的新鲜感和热情极早地就发散掉了,看到的往往是冷漠和失望。但是诗人往往又具备一种自明性,她把那份看透过后的残酷和绝望沉潜下去,韬晦孕育,培养成一种清醒的目光和敏锐的表达。正因为如此,马雁的诗总是透着一股冰冷和残酷的色泽,有时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她的题材和取境往往是很琐碎的生活细节或娱乐活动。但背底里,这些诗又蕴含着各种猛烈的欲望和洞见。正像编者冷霜所说,“马雁的诗镌刻着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虚无的抵抗,和对疾病与死亡的宿命感”,尽管80年代到现在,这将近三十年的间距里,我们生活的中国是那么地贫乏、无聊、穷困和艰难,马雁依然从生命的感悟中发掘出了艺术带给人的绝代繁华以及宿命般的语言秘密。其实与别的诗人作比较,终归是“与我何干”的闲事。但我还是觉得,马雁诗歌的内在艳丽和热量,很像那本19世纪的《恶之花》。为此我也要进一步澄清,马雁(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很贫瘠,我们太缺乏优质文化的营养,马雁本人的生活也堪称平淡,既无大风大浪,又无挥霍堕落或家道中衰,同我们每个人几无二致——马雁对爱欲和死亡的关注尤其与我们凡人契合,但是,她保留了那份生活品质的清洁和语言感悟与书写的敏锐,这就使她的诗歌可以绵延二十余年而愈加精纯和坚强。在庸俗和贫瘠的时代生长出一朵艳异、坚韧的花朵,这种难能可贵正是时代之幸,文学之幸。
说马雁对语言有着高度敏锐的关注,乃至职责感,并非我的臆断。这种敏锐关注和职责感从根源上决定着诗人诗歌的品质和诗句的纯度。在读这本诗集的时候,我在本子上写下过这么一句话,“不以写作为职业/但要以写作为生命/这样才能保证永远自由的心灵”,这大概可以应和波德莱尔的那句话,“我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感到可耻”,我认为,马雁在写诗这件事上抱着同样的态度。她的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过职业性、群众性的繁华与热闹,甚至在我个人十分关注的“五·一二”大地震前后,所有人哭天抢地怆动肺腑之时,马雁那一时期的诗里也似乎没什么表现(根据马雁的履历表,她当时应该在家乡成都,而当时的媒体和文学界,伴随着死亡数字压倒而来的,是漫天飞雪的诗歌作品)。诗人的孤绝和感受的诚实,使得她排除了诗篇中的任何流俗与杂念,而始终保持着平凡质朴的生活向度。
诗人的诗句说明了她/他的一切,此外她/他本人的一生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解释。
对语言的使命感在诗集后面的几篇诗论里有直接的体现,尤其是珠江诗歌节的获奖感言一篇,马雁对语言做了很有深度的解说。她为朋友陈舸的诗集做长篇幅分析解读,她为同时代年轻人在诗歌语言上的努力做鼓励总结,为现代诗歌的语言探访问路,为外国优秀诗人做推介,为自己的语言思考和诗作做现身说明,甚至为古代诗人谢朓、李白等做现代传承。《读谢朓笔记》的开端,马雁分析了《和王中丞闻琴诗》,在简短流畅的文字里对古诗所蕴含的的情境做了跳跃式的精妙分析,初读之时,令我拍案叫绝。可见尽管马雁没有国外留学的学术经历,也没有明确的西学专业学习(诗人是北大古典文献学出身),但她对诗歌语言的结构、形式与意蕴的体会却是非常高明的,昭然可想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影响。
马雁的诗歌常带古风,这既是业之所谓“古典文献”学养的濡染和自觉,也是一个中国诗人所应有文化本能——向古典文学靠近。我们可以没有近现代诗,但决不可没有古代诗。我们必须有现代诗和未来诗,但它们都将由古代诗孕育而出。诗篇里关涉或照应古诗古事的妙词警句、点铁成金,往往成为现代诗情采生动的关要,也是考验一个诗人语言能力的重要标志。非常典型的一首诗写于“2002年春”的《将饮茶——为黄照静和我们共同的荒唐生活而作》,诗名很显然来自李白的《将进酒》,也决定了诗人必定要携带和引领一场潇洒旷达的情思雨潮,尽管诗中的生活场景和经验是现代式的。开篇便是“眼看着,盛夏就要来临,/就要降落在我们想象中的平原。/唱着骊歌的密友们趁着黄昏,/走过平原上倾斜相交的道路。/那些道路最终分开了她们。”诗的经验体现在日常式的智慧话语上,更体现在一种潇洒豪迈的生活词语中,“经验已经总结出了千万条,/我们的智慧从来没有长进过。/忘记了,也就过去了。/读书,临帖,经风,拍案。/草稿纸上不知天高地厚的蓝图,/被残杯倾尽的液体浇灌。”有贯穿古今的超越,又有与自然同化的飘逸与优雅,然后是李白式的借酒(茶)浇出的诗国江山。有此一境,诗的格调也就不低了,所以不管所饮的是“减肥冲剂”还是“玫瑰花”茶,我们的天真、幼稚、无奈与激情,也都溶进了一种洒脱、灵动的生活形式里。结尾诗云,“通过茶,获取钢铁和石油,/采摘成熟的、丰盛的金黄色,获得幸福的生命之涯。”欢天喜庆的收尾,仿佛有着六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豪迈热情,仿佛像海子一样从诗里造出建构世界的物质能量,然而“幸福的生命之涯”一句何其沉重,何人可以承受这宝贵而又精纯的“生命之涯”呢?终究也有古诗里那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情绪抛洒和纾解。
这本诗集从内容到外形,都讨人喜欢,毋宁说,正是诗人在人间的心灵栖所和结晶。朋友们在马雁殁后,尽心于搜集整理,尽力于编排出版,由此才有我们手中的这本珍贵诗集。书末冷霜所写《编后记》也十分珍贵,让我们知道很多马雁诗歌创作的外在状况。将这批“诗选”分为三辑,无疑是非常明智、合理的做法。第一辑“迷人之食”是07年马雁自印诗集《迷人之食》的原貌保存(该印集选诗截止05年),第二辑“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和第三辑“在世上漂泊的女人”分别是《迷人之食》(05年)以后马雁成熟期的作品和之前马雁初期的作品。以我的阅读感觉,第一辑《迷人之食》应当是质量最好的一批诗作,阅读之时,每每怦然心动,赞叹惊骇,隽永无穷。可见马雁对自己的诗作有着明晰的自觉和判断,她知道哪些诗构成了生命的琴弦,哪些诗代表着生活之真。后两辑诗也很好,马雁依然是那样的平实、质朴,依然在一些细微的角落和偶然时刻为我们揭示出生命的讶异与华丽。此外,马雁作诗通常一蹴而就,不惯于反复修改或雕凿斟酌,尽管已经友人校正,我们仍能在某些隐秘的地方看到一两个模糊的错别字,仿佛串联着李白的飘逸之风,由此也可见诗人诗品之一端。
我本想对马雁的一些诗做一下形式分析,因为诗是诗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只有对诗篇本身的感悟和分析才是对诗作最高的敬意,哪怕所解有误,至少也是对诗人“心有所戚”的感应认同。但是一来正如前文所说,诗人的诗句已说明了她/他的一切,无须解析;二来马雁本人对诗歌有着高超的分析感悟能力,我资质驽钝,诗性不纯,强以牛刀解凤,未免冲折灵府。作为一个普通、陌生的读者,正如前文所述,我于诗言诗意之外,多在意作者的生平行迹,故于此再着一点笔墨。
马雁的集子首先让我感到惊讶并长久难以释怀的,有两点。一是她2010年12月28日赴上海访友,30日在闵行区维也纳酒店意外病逝;二是2003年4月马雁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离京回成都生活,并同年9月24日诗人母亲去世。两件事都关乎死亡,都关乎疾病,都关乎某种可怕的想象和念头。注意到第一点,固然是因为(女)诗人辞世的意外、突然,以及年仅而立,也因为那“朋友”、那“探访”,我以为,诗人之死,或者人之死,往往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宿命的自我解说,诗人恰在外地访友期间辞世,这似乎表明,诗人的诗和心是依托世间的他人而在的,或许有一种东西叫“马雁之友”,它构成了诗人马雁的一部分。注意到第二点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触和震撼,当今中国,敏感度和繁华度(或许也是艰苦度)最高的城市,就是北京,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与它有些关系(比如小时候说你爱北京天安门,比如你的朋友或你自己就在或将去那里),它成了我们脑子后角里一根顽固的骨头。马雁是“北大才女”,在北大时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享有声名,又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通常情况下,离开北京回故乡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她的身份是人们称为“人间漂泊者”的诗人。但是命运的事故让她的生命路线发生了转向,为照顾母亲回成都,这足以体现中国文化中最大的道义:孝。一个人有孝心,已经是感天动地了,此人离“贤人”已经不远了;但对于马雁而言,她可能就此长久留在成都。要知道,一旦你住在家乡的城市,尤其是像成都这样的蜀都,你以后就只有这一个出发点,你不得不向东、向北散射全中国。马雁无疑是爱她的母亲的,在一定的年龄层次里,她甚至已经把自己与母亲的残病之躯与自己融合在了一起——在此我又想起“回族”这个标志,我很难像张承志那样去想象这个群体的人对于“孝”和“母亲”有着与我们怎么不同的理解,那仿佛是个悠远的世界,迷人的世界。上天很残酷,让成熟不久的人们不断甚至迅速地面对乃至亲临死亡,这种命运的无力感一定浸透在了诗人的心灵和诗歌里。
马雁要从北京回到成都了,应该是乘飞机,时间是“2003年春”,时年诗人24岁,在《母亲——向北岛致敬》中诗人写道:
午夜,我穿过蒙霜的北京,
踏过地面,不留下脚印。
我愿逆流而上,寻你的爱情,
寻我不存在的出生证明。
在这午夜,我将穿过
大半个中国。飞跃秦岭,
摘二十四年前的花,献你。
我采摘我一生的花束。
这里没有滚烫的物质,
我只葆有这午夜的青春。
我们共有的肾及心脏,
是锁链两端的兽。
母亲,我捆绑自己,为你
做一个祭奠。你是一根鞭子。
在与此相同的时刻,我不能不
抽打自己,舔我们喷涌的血。
我禁不住抄引了全诗,因为诗的情愫很简单,以至于它的首要意蕴很连贯。诗人飞跃从东北到西南的天空,解读着生命的凄苦、不舍、无奈与残忍,追溯着自己与母亲的生命接榫,甚至甘愿自作牺牲,以命抵命,以刑罚与折磨换取母亲的病痛,当读到“我不能不/抽打自己,舔我们喷涌的血。”时,我们立刻被一股巨大的悲怆淹没了,那种恐惧直达心底,已然是超越了生死的生命舞蹈。马雁的诗常常含有这样一种严酷的惊醒,尽管嬉笑打闹、儿女情长也无处不见,例如她还说“水流声如刀刃,亲爱的,/这声音太冷,让我发抖。……我好像死过一回,/像在绝望的刀刃上爱。”(《爱》)她还说,“好像玻璃器皿中的热水,干玫瑰的红/渗开……稀薄的,游离于空无,/寻找那命中的命,血中的血。”(《热的冷——献给soumir,和我的灵魂》),此类鲜红色的向度很容易让人想起西尔维娅·普拉斯或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之类女诗人或作家。又如,马雁写道,
今天,我吃一颗樱桃,
想起一个女人在我面前,
缓慢,忍耐而后大声喘息,
她曾经,作为母亲,
放一颗糖樱桃在我嘴里。
我缓慢吞食这蜜样的
嫣红尸体。是如此的红,
像那针管中涌动的血,
又红如她脸颊上消失的
欲望——这迷人之食。
(节选《樱桃》,2004年春)
半年过去了,马雁似乎仍然活在母亲的阴影里。频繁涌动的血色使得那来自生理、视觉、神经系统和神秘力量的恐惧一再扩张、蔓延,仿佛鲜红的蛇信子即将触到你的脸。然而诗人吞食的是“蜜样的嫣红尸体”,是“糖樱桃”,是“欲望”,生死爱欲,天地伦常,原来都是那样地残酷、生硬,那样地迷人。
我本来可以不谈马雁具体的诗,或者可以谈一下其它的诗,那样会看到马雁的另一个样子,一个更好的样貌、更独特的品质。对于诗人的生平,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细节,诸如家庭、疾病、朋友、工作、经历、恋情以及具体的诗作本事,这些秘密总让我产生各种疑问。但是,就此打住吧,为了纪念这个同时代的女诗人,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去读她的诗。
2011年年初,马雁葬于上海某公墓,同年1月份,我第一次去上海。很刺眼,风很大,很冷,当时我不知道有个女诗人去世了。正像2010年的春天,马雁还在成都,我也在成都,却不知道有个马雁一样。我想,马雁一定很怀念成都,也怀念北京,就像她的诗中不仅有死亡的残酷和冰冷、生活无助的怨艾和忍耐,也有自由游荡的精灵、妙语连珠的谈笑、毫不留情的抗争和痴情缠绵的情爱。
某天下午,读完马雁的一首诗,一首极其普通的诗,我写了一首短诗,附寄于此,聊致爱意与马雁,此诗与上文的评论无关:
十年前的诗人
十年前,诗人抱着她的恋人痛哭
她渴望温度甚于临风而歌
气味刺穿她孤执的幻想
总有枯骨和花伴随一枕清梦
你看,她奔跑着,像没有翅膀的冲刺
她的皮肤红肿,那是一个鲜明的信号
十年前,诗人倚着一棵未开花的玉兰树
哀婉坚强的目光里透出麻木,如燕子
双唇紧抿,流畅的黑发在额前分成人字
她微侧着头,双眉如剑锋轻轻俏起
脖子前的纺绸纱巾像雪堆层层泻落
她攥起手指,手心里攥住一段游魂的命
3.29,13:00,(呼应马雁《怀着一个欲念……》)
4.12,下午
《马雁诗集》读后感(八):马雁:痛苦一种,有诗为证
读马雁:痛苦一种,有诗为证 痛苦就是直接。——马雁《樱桃》 1 向人诉说痛苦是困难的。你说你压抑难捱的青春,说到你不可终日的爱情,说到这座诱惑之都与你母亲一贯的叮嘱,不一而足,这些私密而又普遍的感受,大多时候你只能以几个苍白的感叹词一概而过。神经慵懒迟钝的,过着日常生活,聊聊电视新闻和身边的轶事。而那些敏感的心灵,每个细胞流动着不断更新着的血液,天生如此,要承受异于常人的激动和悲伤,看见被忽略的,听见被诅咒的。这样还不足够,必须历经语言的炼狱才能活过一段生命。写作似乎成为必需,由此,一种诗人就出现在了世上,她努力以语言追求精确的日常;她具了备这样的天赋:敏而多思。 后来,我读到马雁的一些诗,觉得痛苦的言说也就大概如此了。在马雁创作前中期自己编印的诗集《迷人之食》中,《樱桃》是她面对母亲亡故时而作: 我不敢把手探入它的核心, 不敢挖出血淋淋的鬼。 眼望着谎言的清洁。 在这里,否定和悖论的句子,分明如一把匕首,划破皮肤,深入胸膛,然后直视着已经病变多日的内脏。很奇怪,也很有趣,我常常喜欢攫取一些瞬间进行短暂的对比。比如说扎针的时刻与颓败的时刻,比如说骨折的时刻和绝望的时刻,我很想知道,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哪一个来的更凶猛,更容易令人的神经系统抵达毁灭的临界点。两者之中,当然更具体的感觉来自肉体,是所有人的共同经验,写作者得以表达的桥梁,正如马雁的悲痛和爱以身体的隐喻来揭开。但真正的痛苦不是嘶叫和呐喊,真正的痛苦是克制,是隐忍。直到这首诗的结尾处: 我缓慢吞食这蜜样的 嫣红尸体。是如此的红, 像那针管中涌动的血 这让我想到鲁迅在他的散文诗《墓碣文》中塑造的那个吞食自身的长舌意象,唯有手术解剖般的噬心之痛,才能借以显露那些难以表白的精神之痛。而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马雁的诗中更带有许多“粉红色的斑点”,那是女性特有的妩媚和细腻,女性作者善于对细微情感的体察,敏于对身体变化的关注。母亲和挚友相继去世,马雁的生活是不平顺的。如里尔克所说,寂寞是艰难的,爱也是。 2 那些私人的,隐微的情感如义务教育,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一生承受,一生学习,好似烙在生活上的印痕。阳光洒满一地,身体陷进沙发里,如果这样无所哀思,无所关心,倏忽一日也就过去了。可是当一个人跳出所谓的“小天地”,投放视野于社会万象和生命万物时,拥抱情怀的代价便是痛苦,是更巨大的痛苦:如一个西西弗同时推举着一百个滚石那样。青年批评家刘阳鹤在他关于马雁诗歌的论文中谈到:“正是这种情怀,才将她塑造成了一个承受着世间痛苦的诗人形象。”此类带有世间关怀的作品,大多出现在马雁后期的创作中。马雁常年耽于语言的“炼金术”,此时,勤奋的练习已经使她的写作臻于成熟,同时视野更加广阔,洞察力更加敏锐,面对一座巨型的“冰山”,既能内化其显形的轮廓,亦能勾引出隐藏在“冰山”之下的“宝藏”。例如在《北中国》一诗中,她先取景于“盛大的气象”,镜头不断地拉近铺展,直至最后聚焦在一只在土地上打滚的“土豆”。这种放大镜式的观察,具备了气度,也未失掉爱心。我想起电影《蜘蛛侠》中那句有名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爬行穿梭于城市交错的甬道之间,与黑暗势力相互寻觅的同时,帕克也感到,与责任相伴的还有钢筋水泥般的压力。同构地想象,马雁孤身行走在北中国,与苦难的河南人和河北人一道,与沉重的山东人和山西人一道。 3 马雁因病早早逝世,许多人扼腕叹息。她的才华横溢,在诗歌艺术上追求和达到的成绩带给大家惊喜。刘阳鹤首先推荐我读马雁的诗,并说她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的回族女诗人。也可能我记忆有误,已经不能清晰出他在跟我介绍马雁时,是否有这么多的修饰语。修饰语同时也是限定词,是标签。可是我相信,不论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行走在大地上,一些艰涩和犹疑的人生感受大多是相同的吧。在马雁的诗作中,并无许多专门对民族情怀和宗教主题的抒写。我也只注意到“裹尸布”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在她的诗中,以这一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抒发她的预感般的、隐秘感受。甚至在她一首作于03年的诗《是的,我必死》中,我读到: 他穿神的战袍, 说一个字, 竖起一根手指。 ”一“,永远不能 出现为”二’。 在某些层面上,我愿意将其解读为信仰者与挑唆着的恶魔之间的对峙。向死而生者或许被人讥笑为愚蠢,讥笑为不可救药。而她最本质的意义也正是在纠缠和守候中实现的。 事物仍在流转,而斯人已远去。现在,纪念她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她的作品。提起她,我与许多人一样,不由地悲从中来。愿真主饶恕、慈悯马雁,一个痛苦而悲悯的灵魂。 March 2015
《马雁诗集》读后感(九):旧诗集
旧诗集
一直不敢打开的诗集
打开了,有一个手印
在<玛格丽特与大师>那首诗上
“谁是那年春天妆扮她的洋槐花?”
谁?是谁,哪个惨淡灯光下的
装订工的小脏手——她的
洋槐花,先于我读到一些
与死神砌茶下棋的句子
她留了两眼,一口气,活着。
封面上枯瘦的画像不是她
除了攥紧的拳头。
“这是最后一夜,我再也不迟疑。
这是厌世者统治的世界,我也不再
穷于隐瞒。”那些融化
近乎光的花都是她隐瞒的,
我把手比了一下手印
恰与旧冬天我握进口袋里她的手
一般大。
我握住了,手指冰冷
一一松开,死神她在喘息。
雨雪在那件旧大衣里
淅淅落下,窸窸化作无有。
——莫斯科是存在的,
我写过<赤都心史>,
你我分饰了一角。
那里的人因为酒醉
始终拒绝每天签发的永别。
2012.10.30.
《马雁诗集》读后感(十):念马雁
昨晚,几个朋友在书店里窝着,等跨年,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突然想起三十号是马雁的忌日,她去世也五年了,给大家读一首她的诗吧。朋友笑:“你呀你,关注的诗人不是过世的,就是去世的。”我惭愧,真是。一个诗人需要用死亡才能唤起别人的注意,也实在是让人心疼。至于因为“死亡”才去读诗的人,心里多少也要愧疚一下。
马雁不喜欢用“纪念”这个词。说起来,我第一次知道马雁,实际上是因为马骅。到这里,忍不住想回溯一下走进这两个人的过程,很有意思。
零九年在荒岛,第一次读到了蔡天新老师编的《现代汉诗一百首》,很喜欢,尤其是里面马骅的《乡村教师》,干干净净,动人。“十二张黑红的脸蛋,熟悉得像今后的日子/有点鲜艳,有点脏。”这两句一直晃在心里,忘不了。想想几年后会去青海支教,也多少与此隐隐相对。
我去搜他,才发现网上已经把马骅捧为“乡村最美男教师”了。倒是几篇老朋友的怀念文章,让人安安静静的感动,特别是马雁的《想想你,马骅》,应了我前面想说的话。她说:“纪念,这样的说法非常滑稽。的确,假如我们这样的人消失,也只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公众的事情。使用‘纪念’这个词语就显得荒唐——没有什么人会去纪念,我们有时候会去怀念,但怀念就意味着接受了时间的隔绝,那漫长的距离就此形成,所以我很久以来已经学会了不去怀念任何事、物。”现在,把这些话返到马雁身上吧。我掰着指头数过去的日子时,其实,她已经慢慢远了。
我记得马雁刚去世时,还有很多人在絮叨她,感慨不已,差点演又变成一场“诗人短命”的论述。好在人健忘,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我从马骅那里,又跑到马雁这里。她的豆瓣之前就关注了,喜欢她的那些书评。她有古典文学的底子,又写诗,文字其实不大好读。但读进去一点,就莫名叹一声:“好。”
后来,未名诗歌节要给她做一个纪念性的活动,我自然是要去。坐在台下,听很多她的朋友在台上读写给马雁的诗。当晚要赶回天津,我不能坚持到最后了。在出口,看到一个魁梧的大汉,我问:“现场有没有马雁的诗集或者散文集哪?”他摇摇头,提前印的都发给嘉宾了,我叹口气。然后,这位大汉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南开,他说自己是天大的。我哦哦了几声,溜走赶车去了。后来,才知道,魁梧大汉是秦晓宇师兄,《马雁散文集》是他编的,后悔当时没多聊几句。
读马雁的诗和散文知道了更多马骅的事儿。她的诗我并不能都懂。不过,关于马骅的两首,每读每难过:《冬天的信》和《夏天的信》。写夏天那首诗时,马骅已经掉入澜沧江里了:
去年,在黑水我想起
一个梦,汹涌冰凉的江水穿过陡峭的山,
人们在谷草丛中等一月一班的公共汽车。
我住在那里,荒凉而绝望。是的,你
住在那里,荒凉而绝望。你的鱼鳞云
没带来爱情,今天我在这里写夏天的信。
当冰凉的江水冲刷你时,有一个人不断
给你写信,到天起凉风时,给你写信。
昨晚读的是《冬天的信》。朋友嘈嘈杂杂,正热闹着过年气氛,没来由被我读了这么一首,有些沉默。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这让人安详,有力气对着虚空
伸开手臂。你、我之间隔着
空漠漫长的冬天。我不在时,
你就劈柴、浇菜地,整理
一个月前的日记。你不在时,
我一遍一遍读纪德,指尖冰凉,
对着蒙了灰尘的书桌发呆。
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
也像我们这样,平静而不痛苦吗?
她知道半年后,自己这位“任性”的朋友会突然间再度“消失”么?哎呀,这些话,自己真有点写不下去了。“死”这件事是亲者才能真正触摸到那种痛的,对于外人,越写只会越过情,没意思。再说,我看马雁也未必喜欢这些“哭腔哭调”的玩意儿。罢了,罢了。
我喜欢诗集后面那部分诗论,说得很贴切。
譬如她讲:“一个诗人要努力让自己不与黑暗合而为一,用他的敏感和力量,使他成为一个有资格、有实力深入到人类最丑恶的地方去的特选子民。”
她讲:“我不喜欢沉浸在细节里的那种愉悦,喜欢简单直接,一阵见血,当然也可能并没有什么血可见,那么给出这个空也是对的,给出毫无惊奇的现实。”
她讲:“谦逊,满足于简单,不急于给出自己根本没有的东西。”这句真是清醒,自己就做不到。
她说:“写诗是一种冒险,这是最没底线的一种冒险游戏……语言可以拯救一切,甚至我们自己。”
她说:“这个世界过于整饬,以至于多数人都为此感到厌倦和劳累,每天在同样的世界里行走的是可怜的囚徒。诗歌应该有这种野心使他们获得解脱。”
她说:“我常常想,生活是如此复杂,我对痛苦和幸福的体验虽然微不足道,但却真的想要书写下来,甚至通过有限的诗歌技巧使这种书写成为一种提醒和创造。因为力量的有限,这种提醒和创造往往只是自我之内发生,但谁不是如此呢?就像那些不断回忆或者聊天的人们,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资源,是情感的源泉。”
如果可能,我想多摘一点给大家看,去读书很多人又没耐心了,我自己有时也这样。马雁对于写作足够认真。诗集前面有句话:“每写下一个字都冒着生命危险”。我想去读读她这些踩着刀刃的文字,值得。
比起诗,她的散文我更喜欢一些。大概诗需要性命相搏,我畏缩不敢向前。散文好一些,没那么大杀伤力。
厚厚一本,那一年翻来覆去读了很久。实在是没法拒绝她笔尖那种跳脱的语调,用她自己的话是“跌宕自喜”。貌似跑野马,却也飘飘洒洒,兜兜转转,不离主旨。写散文的她轻松活泼地像个邻家大姐姐,机灵亲切。许是自由,一篇文字,她入笔常常宕开一下,写点杂事,不等你清醒,她已经瞬间把你调回了文本。我领略过好多回,常常自己乐不可止,惊叹她行文的这种洒脱随性。
散文是真好,比起诗来,也易读。不读,就错过一个好作家了。
说到她的写作,我自己倒是开心起来了。是啊,阅读始终是有快感的。所以,我会都特别感激每个好作家,是他们让自己一点点饱满起来,没那么面目狰狞。每个写东西的人,也乐于看到自己的文字能流进别人的生命,重新欢畅吧。
自己如果去上海,一定要去马雁墓前,给她放一朵花:“谢谢你写下的这些。”
一月一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