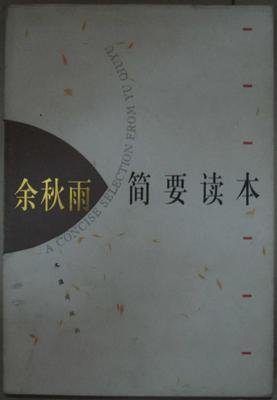
《山河入梦》是一本由格非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山河入梦》读后感(一):【七月读书】山河入梦
【谭功达】 梅城小镇,他寻着母亲的传说。 母亲对于他,时远时近。近时,她存于梅城妇孺皆知的唱词中。远时,即使在唱词中也只寻得关于母亲的一鳞半爪,真真假假,让人恍惚生疑。 身为一县之长的他,不懂人情相处,勾心斗角。超前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落得民怨四起,苦不聊生。 爱情于他,也像是一阴晴不定的河,时而干涸,时而如小溪潺潺,时而又如洪水般猛烈。 他恍若赤子,又如稚子。 面对丑恶不堪的批判,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他心思游离,只是看着台下新来的女孩,眼里沁出一片青光,身体摇摇如醉。 哦,他还是个女痴。 【姚佩佩】 姚佩佩自觉没有白小娴的天鹅颈和仿若圣物的清白和淳质。她只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分子,原先澡堂卖筹子的。 她是紫云英和苦楝树的阴影,心有沟壑难隐,却也隐隐约约渴望些什么。 她是从什么时候看上了他这个女痴呢,明明看起来呆板木讷,还总做一些异想天开的事。可她还来不及察觉,爱就轻轻的趁着黑夜来了。 而她之于他,虽没有白小娴如皓月般的想让人仰望得到,却也莺莺燕燕,别有韵味,让人心旌摇动。 【他们】 也许他们初遇时的第一眼便早已为以后埋下伏笔,他是她心底的佶屈聱牙的影子,她是他夜晚辗转反侧的月光。 可惜他们谁也没想到结局。 他和姚佩佩,终是两个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人。 他们浪漫,现实压的人难受。 她说:“逃,逃,逃,去无人的小岛。” 他说:“带上我,就我们两个。” ——如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下何曾不是两颗早已相互吸引的心,无奈他们终究没有抓住那一刻。 日后物是人非,云泥两隐,他的花家舍是表面安稳实则暗流涌动的巢穴,而她的逃亡所带来的终极自由,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 那本该在蟋蟀和金铃子的叫不停的夏日,院中摆两把竹椅,周围种满了紫云英,看着金粉一样的星斗,听她讲怪话的夜晚,不过是想象中的梦。 罢了,罢了。 他最终明了,他和母亲的路,终于重叠。 【格非】 作者格非,真可谓意识流小说大师,读他的作品忽略时代感,明明该是时代感和政治意味浓厚的时代,他却独辟蹊径,不自觉将读者的视角关注在个人身上,由个人的遭遇与时代本身造成的巨大反差,由近及远,揭开宏大的历史背景,惋惜却又无可奈何。 他细腻而感性,如果说从《山河入梦》中读出什么,我想说是倔强。 看似凄美的故事背后,是他暗藏的冷剑和悬崖,伴着讽刺和笑,一笔一笔勾勒上色,无形中便是山河。 读罢叹息, 书中的人一生无论怎样宏大,水煮浮沉。 对读书人来说却也只像是一壶清茶,一场雨的间隙。 翻上书本, 就这么过去了。
《山河入梦》读后感(二):梦醒时分 - 山河在,人已非
《山河入梦》,格非“江南三部曲”之二。前半部分的文风较之第一部略有不同,更注重故事情节的推进。个人比较喜欢第一部清雅舒缓、笔墨之下江南韵味萦绕的风格,这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又得以回归。就故事情节而言,《山河入梦》却是三部曲中最为夸张、冲突性最强、也最为荒诞而又寓言性十足的一部。
曾有人建议将此三部曲命名为“乌托邦三部曲”或“桃花源三部曲”,如果只读第一、第二部,确实未尝不可,尤其是这第二部,时间跨度从1956年至1976年,作者把笔墨浓缩在“梅城”这样一个江南小县城、“谭功达”(第一部主人公陆秀米之子)这样一位充满“乌托邦”式幻想的县委书记身上,将主人公追寻“乌托邦”或者说“桃花源”的梦想描述的淋漓尽致。小说以一条明线 - 谭功达对改造梅城的“桃花源”之梦,和一条暗线 - 谭功达对姚佩佩欲说还休、心有戚戚的情感之梦,编织出了主人公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看似荒诞但又不失真实的人生之路。
在这个刚刚解放没几年、尚未能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的小县城,谭功达以县委书记之名修建大坝、开凿运河、通电通气、豪情万丈地计划五年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结果可想而知。他这种不可理喻的执着,导致被撤职下放,看似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冥冥之中,这就是他的命:只有这样做,这样走,最终他才能如同母亲一样,走向梦中的“花家舍”,走向那个似是而非的“桃花源”。
陆秀米时代的“花家舍”,是由一帮土匪靠打家劫舍维持的“桃花源”,在貌似田园般与世无争生活的背后,是匪帮六兄弟明里暗里的勾心斗角、你死我活;而谭功达时代的“花家舍”,却是一个貌似公平公正、衣食无忧、以自觉劳动为光荣、以利他主义为风尚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每个人都如同机器,不苟言笑,谨小慎微,因为他们生活在“101”的严密控制之下。
陆秀米会满足于这样的桃花源?谭功达会接受这样的世界大同就是他的梦想?
小说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陆秀米从花家舍出发,走向自己的革命之路,最终回到故土将自己的心囚禁了起来;谭功达从花家舍出发,走向故土,走向最终的囹圄。
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个体对命运的抗争和改变,几多成败,几多苦痛!
魂归故里的那一刻,梦醒时分的那一刻,谭功达依稀听到已经被判死刑十几年的姚佩佩对自己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 - 这个社会呀,
没有死刑
没有监狱
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化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
......
梦醒时分,山河在,人已非......
《山河入梦》读后感(三):山河入梦,山河如梦。
茅奖作品,构思文笔叙事人物等的长处自不必多言。
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也许对作者而言具有很深的影响极大大的意义,可他似乎忘记了还有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群体,只能调取历史书上仅有的介绍来帮助理解书中的时代背景。读完后深感‘头重脚轻’,‘前慢后快’,前面略显拖沓,而后面特别是理想中桃花源的描写有点无力,甚至多用直白的陈述句。挖的坑也没有填完(数字减法那个),还是没有避开世俗甚至低俗的一些情节。哀男女主人公们的不幸,怒老谭之不争。
不过嘛,,悲剧作结留有遗憾也是我想象之中的,总之,赞٩(๑❛ᴗ❛๑)۶
《山河入梦》读后感(四):山河破碎风飘絮
近来晚上一直受蚊子君叨扰,收了数不清的红包,但也因此有了负气早起读书的福利。《山河入梦》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主人公谭功达是上一部主角秀米的次子。谭功达是李云龙式人物,打仗应该挺厉害,但小说开始已是他任梅城县长,管理政事却甚是一般,冒进、不接地气、不听民意,很有想法但基本无法贯彻实行,最后稀里糊涂被罢了官。对美女没有免疫力,好像对姚佩佩心有所属,但缺乏决断,跟着势走,见一个爱一个,最后稀里糊涂双双被毙。时代的悲剧,爱情的悲剧,个人的力量都无从逃避也无法选择。上世纪那个时代的洪流,卷走了多少这样曾经的“英雄”?从这一点上,是个大大的悲剧,较第一部《人面桃花》,有着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但和余华《兄弟》相比,尽管《兄弟》也因后半部太粗糙太荒谬广受诟病,但其人物塑造、大场面的铺陈方面,都要略胜一筹。尽管格非在清华大学主讲小说叙事学,我却觉得他更适合写散文,情节架构不足,人物立不起来,但语言感觉不错。 考试,是学生的难日,却让我有了半天闲暇。读完一本书,总会有这样的感觉,相比之下,此时我们的重压、烦恼和苦闷,其实,并不算什么。原来,于我,读书的过程,也是解压的过程。
《山河入梦》读后感(五):第十三道门
第二部虽然在人物和风格上继承了第一部,但对花家舍的描述,远远超过了第一部,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几乎没有任何避讳的白描和批判,在郭和谭的最后对话中,刻画得入木三分。“主义”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人性”。十分巧合,看读了FT的文章,说的是列宁主义和金融资本在过去100年和10年都曾试图用普世的谎言掩盖事实的真相,无论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能够解决人性的根本问题。从这点上,作者用第二部的“花家舍”管窥了所谓“社会主义”消亡的必然。
当然,用“红楼梦”的眼界看主人公,依旧是那个“宝玉”似的花痴,一个由大上海大户人家沦落的女孩,一段荒诞却宿命论的婚姻,都是可圈可点的。结局无需过多在乎,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地位和法律准则本就任人践踏,任何侥幸躲过迫害的“真情流露”反而显得不真切。
“紫云英”萦绕,究竟指向何处?“第十三道门”,开不开?
《山河入梦》读后感(六):总有理想者败于时代,不管这个时代是好是坏
知识分子作家都有野心于表现宏观历史的通病,或者称之为情怀或志向,小人物的悲欢、个体的境遇不过都是外衣。从某个角度说,诸如格非先生的作家群体也是理想主义者,立言是他们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
理想和善良,有时被诩为必不可少的美德,有时也被诟病为害死人的缺陷。谭县长是善良的,作为一个四十多的老男人,纵然沦为被那些青春的花季少女嗤之以鼻的花痴,他并没有玩弄她们,却也从不会得到她们的同情,除了佩佩。他并不呆傻,他可以料想任何龌龊和苟且,只是从没去做。就像人区别于禽兽,发乎情、止乎礼,是他区别于钱大钧和那个姓金之流的所在。
云泥两隐,作为爱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初时总感新奇,细想又觉恍惚。是什么让佩佩爱上谭达功的,也许是那些满是佩佩的纸片,也许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泥人,也许是那晚小岛隐居的笑谈,但他们终是被恶意的命运错开了。谭达功与白小娴之间的爱情才是真正的霄壤之别,谭佩的云泥两隐,才让人神思。
总有理想者败于时代,不管这个时代是好是坏。不过还好,还有人坚持自己还没有到妥协的那一步。
《山河入梦》读后感(七):世间再无花家舍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作为江南三部曲,若单独评论一本书必然内容上有所缺失;可同时深入评论三本书,一篇小小的书评是装不下的。在此就花家舍这条主线谈谈,因为三个主角都去过花家舍,虽然每个人来时状态不一。
一、《人面桃花》——梦想初启的陆秀米
陆秀米来时的状态:普济村陆家小姐陆秀米在被花家舍土匪绑架之前,经历了父亲发疯(1898年,可能暗喻维新变法的失败),表哥张季元惨死(1901年,暗示革命党人的失败),刚对世界懵懂之际即遭横祸,尚未理解人间之事就已形容枯槁,任凭母亲嫁人处置。
花家舍的初衷与现实:官场退隐的王观澄营建花家舍的理想在于实现桃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典型的小国寡民。但这种经济之策无法长久维持,不得不依靠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意。结果桃源成了土匪窝。
外人眼中的花家舍:在梦想初启的陆秀米看来,花家舍是自己曾经梦见过的地方,也见到了父亲理想中连接各家各户的长廊,身体虽然被囚禁,但心灵在此处却得到了释放。临死前的王观澄如此托梦开导她,“那是因为你的心被身体囚禁住了。像笼中的野兽,其实它并不温顺。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虽然王观澄不希望陆秀米走上自己的老路,但已明白命中注定陆秀米会继承他的事业。
离别花家舍之后:懵懂的陆秀米在花家舍继承了父亲、张季元、王观澄的梦想,回到普济后成了陆校长,即使“他们和各自的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这意味着觉醒的时代(1904年)即将到来,尽管陆秀米自己不断遭人唾弃与背叛,乃至落得孤家寡人。
二、《山河入梦》——梦想坚定的谭功达
谭功达来时的状态:梅城县长谭功达在成为花家舍巡视员之前,一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修水库,建沼气池,开凿运河,不断地开会去解决他眼中的头等大事,结果落得个灰头土脸的丢官下场。而心中则一直压抑着对秘书姚佩佩的感情,毕竟他是个如贾宝玉般的花痴。
花家舍的初衷与现实:军队首长出身的郭从年建设花家舍人民公社,是希望能实现共产主义梦想,人人出力,自我监督,为公社心甘情愿地奉献。可花家舍却成了相互监视的牢笼,“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公社脱离了郭从年的掌控,逼迫着郭从年同意进行围湖造田工程,作为笼罩在所有人心中的一片阴云而存在。
外人眼中的花家舍:初抵花家舍的谭功达甚是兴奋,梦想中的共产主义成了现实,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回廊之间有便民雨伞备用,人人自觉上工报工分。不过时间一长,他也意识到不对劲,戏台上永远只有白毛女这一出戏,即使在湖心谈话也可能被人告密,《101就在你身边》,他隐约感觉到恐惧。
离别花家舍之后:梦想坚定的谭功达在花家舍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体验,终于决心直面姚佩佩的感情,虽然最终天各一方。不过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他依然保持着梦想,即使身陷囹圄也不忘进献“梅城规划草图”。1911年谭功达出生时革命开始,1976年他离世时革命终结,他的死亡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春尽江南》——梦想幻灭的谭端午
谭端午来时的状态:鹤浦市诗人谭端午进入花家舍之前,青年时期的诗兴早已磨去,对家庭事务也不上心,对小辈友人绿珠的乌托邦理想冷嘲热讽。虽然看似是个悠哉游哉的人,但身缠琐事,房屋纠纷,婆媳矛盾,纷纷杂务,读一本《新五代史》竟然花了一年。梦想与人生幻灭的同时又不得不背负各种责任。
花家舍的初衷与现实:王元庆和张有德合伙盘下了花家舍,前者希望能在花家舍实现“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后者则坚持将其打造成“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终于张有德逼迫王元庆撤资,在历史文化名胜的牌子下建成了高级会所。
外人眼中的花家舍:谭端午是在友人的劝诱下来花家舍参加诗歌研讨会,夜晚见识过了暗藏僻静之处的声色场所,白天则又看到那些风尘女子成了历史重演舞台上的演员,荒谬至极。
离别花家舍之后:花家舍并未给谭端午带来任何改变,反而是会议间隙与前妻的坦然交谈,让他起了回忆梦想的念头。终于他续写了二十年前(1-9-8-9年)未完成的诗稿,祭奠那逝去的理想。“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四、世间再无花家舍
1904年陆秀米在花家舍觉醒。即使她已经看到了梦想的虚伪和艰险,但于她而言,梦想可以让她逃避令人窒息的老宅,可以让自己与父亲、张季元和王观澄离得更近,让自己有所依靠。
1966年谭功达在花家舍惊梦。当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他觉察到郭从年所言的公社恐怖之处后,他选择了听从内心欲望,但毕竟一辈子都在干革命,依然在死前都放不下革命事业,虽然革命的时代终结了。
2009年谭端午在花家舍回忆。花家舍已经没人来向他托梦或讨论梦想,因为梦想本身已经被掏空,沦为了供人娱乐的销金窟,而在花家舍外,“与妻子带给他的猜忌、冷漠、痛苦、横暴和日常伤害相比,政治、国家和社会暴力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家庭的纷争和暴戾,作为社会压力的替罪羊,发生于生活的核心地带,让人无可遁逃”。
花家舍一直纠缠着陆秀米、谭功达和谭端午这三代人,从觉醒到惊梦再到回忆,梦想从高高在上到被人遗弃,理想主义者或者诗人成为旧时代的遗老遗少。
世间再无花家舍。
《山河入梦》读后感(八):《江南三部曲之二山河入梦》评论-22分
第二部看了四天,故事的人物是承上启下的,但内容并不算有太大的关联,只是在描述不同的社会时期中国的样子。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复杂的,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会走弯路,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秀米的儿子谭功达,依然追求着母亲曾经的理想,也如同他的母亲一样,最终失败。
这部的文字风格变化很大,第一部唯美而文艺,这一次非常的写实,推进情节和描写更加的细密,更适合于表现离我们近处的事物。
这段故事从1956年说起,是中国迅速成长和变迁的时期,谭功达县长,年过四十,有原则讲规矩,但问题在于他过于的理想化,修大坝,挖运河,建沼气,甚至设想到公用电话,这些理想确实在多年之后都实现了,但在特定的时代里却是不切实际的。再远大的政治理想,也要滋生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如果吃饭穿衣都费劲的情况下,就必然得把理想先搁置起来。
书中的更多笔墨写男女,封建社会的弊病在这个问题上展露的淋漓尽致,社会性质在过渡的时期里,严苛的观念上的压制使得物极必反,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谭功达人到中年,还没处过对象,也不会处对象,白小娴头回去他家,就把人家给扑倒了,扒了裤子,咬破了白小娴的嘴,本来很浪漫的一件事儿,结果差点整成强奸,本性展露无遗。之后又没经得住寡妇张金芳的勾引,破了处男之身,只得与之结婚生子。可谭功达的心始终在姚佩佩的身上,甚至大于他的人生理想,最终的结局也毁在女人的手里。
男女之事在这本书里被描摹的灾难化了,金玉下药拿下姚佩佩,金玉因此丧命,姚佩佩逃亡。钱大钧勾引汤碧云,汤碧云流产,事情败露。张金芳在结婚之后,和隔壁杀猪的住到了一起。谭功达因为包庇姚佩佩毁了自己,也牵连了高麻子。书中半数的人物,都因为男女关系的把控,而成了悲剧。人的本性不能压制,憋着早晚会出问题。
花家舍郭从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是需要有个性的,是要彼此区别的,这才是生活,而在花家舍的体系里,终极理想是把人都变成了机器,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活着的乐趣何在呢?
《山河入梦》读后感(九):政治爱情与1984
政治爱情与1984
原本想使用“荒唐的政治 可笑的爱情”这个题目的,想法产生于p270-271姚佩佩被省委秘书长金玉迷奸之后,姚佩佩在衰弱中用玻璃将熟睡中的金玉双目刺瞎的段落。可以说,这是小说最大的转折点。至于随后姚佩佩在逃离时,为摆脱瞎了眼的金玉的纠缠而用石头将他砸死的行为,远不如刺其双目过瘾。因为尖锐的玻璃是取胜的关键,就像曹操准备刺杀董卓时的紧张感一样,一旦刺下去,其引起的快感比杀死对方还强烈。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羚羊。结了籽的油菜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
以上这几句逃跑的文字承续上文的快感而来,具有美丽的轻盈之感。正体现出格非从来就有的诗性向度。
而后,姚佩佩逃亡,谭功达外调下放。小说情境从梅城的政治场域切换到富有浪漫社会主义气息而又蒙着一层诡秘气氛的花家舍人民公社。谭功达的政治目光以及与姚佩佩的信件交流,都笼罩在虚无缥缈之中。 小说的格局由此一分为二。
这便是读完后我又把题目换成“政治爱情与1984”的原因。
话说这部《山河入梦》在结构起伏上资质平平,在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小说既没有《人面桃花》的神秘和神经病态气质,又没有《春尽江南》的不断翻转、暗线密布的繁复机密。相反,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写起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梅县县委班子里的气候变化和个人性情,着意刻画了陆秀米之子谭功达的情感问题在政局中起到的调和作用,同时牵引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秘书姚佩佩线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如赵树理、孙犁、梁晓声之辈,早已为文学史所抛弃和诟病,但当2000年代的人再去描写当时的社会时,也自然回到了那种带着禁欲主义和假模假式的空气当中。那是一个平淡乏味、人性道德都被蠹蚀得虚伪的时代。格非似乎也没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妙方。
但是格非的先锋结构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就是他经常在触觉、嗅觉、心理活动、文字或符号游戏,以及蒙太奇式的情景跳跃中,减轻了社会主义小说固有的那种呆板和僵化特征。
很难确定格非为什么会选择从“县长、县委书记”这样的政治身份切入小说,也许是格非骨子里具有的历史意识、家族血统意识,使得从陆秀米的父亲以来的所有主人公都必须有着显赫或神奇的出身与身份,才能让他们展开拳脚,对“桃花源”“花家舍”“乌托邦”一类的社会理想产生幻想的能力,并试图去实现它。
从下乡考察、公社化实现率、农民破坏公社化以及私自包产到户、运河开凿计划、发电厂计划、沼气池计划,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从毛泽东肇始的那种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幻想家热情和社会主义初期的狂热,另一方面也似乎看到了路遥的影子:书记如何,县长如何,县委大院如何,省委领导(尚方宝剑)如何指示和开会,副县长和县长之间的明争暗斗,传达室的大爷如何,女秘书如何……社会主义都会没完没了地写这些东西,而作为核心人物的政治家往往怀着救济黎民、改造现实的胸怀,偶尔放松下来抒情之时,必然是站在山岗或者酒楼的高处,眺望着古旧的城墙或老城区,以感发任重道远、责任重大、社会主义宏伟蓝图若隐若现之慨。
这样一描述,仿佛共产党的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当代的一个杜甫。可是这本身又是极其荒唐的。因为,共产党人的七情六欲时时在他们身上作祟,于是有时是通过“革命大道理”撺掇起来的革命关系,有时又是呼啦啦大厦将倾、千人踩踏万人攻击的作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局大变换。
谭功达这个人物,一开始便被格非赋予了一种“花痴”的天性,像贾宝玉/西门庆一样,典型表现就是,一见到貌美肤白的女孩子,就像看到神仙一样怔怔发呆,忘情注视。
格非没有交代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是怎么一开始就当上县长的,从背景交代里可知大概是因为昔日战功。因此从一开始的描写中,难免就处处伴随着一种带着身体摩擦感、羞耻感的心理活动,往往是快感和羞耻并存。由此也决定了他和几个女性交错展开的关系,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小韶,虽然格非似乎并不擅长相貌描写,但从男性身理和心理反应来看,应当皆是闭月羞花,尤其是眉目灵动、皮肤雪白、身材窈窕。
谭功达在性心理、理性气质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大男孩。然而他却是一个已经四十岁的单身汉。
而在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气候里,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干部背后,往往又必然有各自的势力支柱。谭功达的靠山,就是那位不曾露面的聂竹风聂老虎;而副县长白庭禹、钱大钧却是通过阴谋的手段,极力攀附省委秘书长金玉。(一开始,作为浪漫革命家谭功达的对立面,还有一个实有文墨的副县长赵焕章,可惜很快就被排挤掉了) 作为一个思想纯洁、热情饱满的大男孩,谭功达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太单纯,因此从一开始就走进了阴谋家白庭禹、钱大钧和金玉等人设下的圈套,甚至直言敢谏的赵焕章被排挤,可能也是他们为端掉谭功达而走的一步棋子。而一旦他的靠山不稳定了,他就有被翦除的危险,正所谓“荷尽已无擎雨盖”。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除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各项事务之外,谭功达像个等待成亲的年轻人,被白庭禹、钱大钧之流拉进了一个“相亲”的氛围之中。于是,跟姚佩佩之间的关系和小心思,跟白庭禹侄女白小娴之间纠结而尴尬的交往,就成了一部具有浓厚“社会主义革命情感”色彩的“政治爱情小说”。
在这其中所牵涉的各色人等中,政治成分、家庭出身、户口与政治面貌等,又构成了一层敏感的气候。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三个女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危机,这种危机始终影响着他们对待爱情时候的表现和抉择,并于那种少女本能的爱情观进行交锋厮杀。
事后看来,貌若天仙的白小娴是白庭禹布下的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异常活跃,主动出击,并险些成功;楚楚动人、机灵活泼的姚佩佩是钱大钧利用了谭功达的一个善举,而顺水推舟布下的另一颗棋子,这颗棋子比较暧昧,但比起白小娴那种激烈和直白的“意识”,它更是一个深深潜伏、欲说还休的“潜意识”。
政治意识不够敏感的读者,读完小说之后恐怕也看不出这些阴谋,因为格非也没有明显提示;但是仔细回想一番,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道德生态中的肮脏与无耻。你几乎可以条件反射似地联想起《平凡的世界》里那种政治联姻的种种考虑,联想起《芙蓉镇》里的人人豺狼的恐怖气氛,联想起《天浴》里革命干部对女性的压榨和谋杀,联想起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史料中数不清的强奸、霸占的数字。但是你很难联想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因为王小波实在太离奇、太奇幻了,它从文字本身就是搞笑、解气的。但是道德罪恶的沉重还是要正视,因此,读到p270-271的时候,这一串联想让我写下了一段话:
“无论是看历史资料还是看艺术小说,都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社会主义风气中充满了卑鄙阴谋、荒唐滑稽、男盗女娼、无耻下流和诲淫诲盗,其在人类天空背景下的道德品质甚至远不如勾栏青楼、岛国毛片、陆家嘴酣战来得纯洁高尚。”
为什么会有这样气愤的感慨呢?因为不仅仅是金玉这样高高在上、阴森丑陋又内心肮脏的省委干部的污秽的欲念和阴谋,正是白庭禹、钱大钧这样的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将人性的丑恶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白庭禹老谋深算,为了笼络、扳倒谭功达,不惜牺牲在文工团跳舞、对爱情还懵懂无知的20岁侄女白小娴,并以此为地主出身的哥哥嫂子的政治出身增加安全筹码。白小娴是一个极有趣的女孩,很有脾气,为了全家的生存委曲求全,从断然拒绝到主动向谭功达投怀送抱,以及耍恋爱中的小脾性,期间还差点被优雅的舞蹈教练王大进诱骗……然而当谭功达大势旁落,遭到白庭禹、钱大钧全面反攻和栽赃陷害的时候,这个傻傻的女孩表现出了天然的耿直、正义和烈性:坚决拒绝写材料诬告谭功达“强奸”,因为反而是姑父姑母当初的教导使她区分了强奸与正常爱情表现的含义。而姑父落井下石的污蔑,是违背事实的。
钱大钧也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徒和伪君子。他和谭功达本是革命战友,还在战争时期的作风问题中受过谭功达的不杀之恩,但此人不仅恩将仇报,参与政治阴谋,而且私留后花园(《人面桃花》中薛举人的旧宅),诱奸落后分子汤碧云,事后又在人前装模作样。汤碧云本是心性卑劣的人,与姚佩佩结成患难之交,但经过钱大钧的糟蹋、遗弃和政治交易,变成了政局性交易阴谋的帮凶,出卖姐妹,最终将姚佩佩推下命运的深渊和逃亡之路。
在格非若隐若现,看似毫不连贯的叙事线路中,两条灾难的线索先后扭结在了一起。
谭功达好大喜功(就像毛泽东那样),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建设想象,又早早地被县委大院里的一帮阴谋分子通过暗中勾结省委秘书长金玉、美人计缠身等手段排除在外,谭功达虽然有所耳闻甚至接到过许多匿名信,但本性天真的他也无计可施。最终连日暴雨时,在一场像是刻意安排的困局和昏睡中,谭功达因错过了下乡抢险救灾而被解除职务。白庭禹、钱大钧顺利晋升书记、县长职位,在将谭功达逼得没有容身之所得同时,又极力组织对谭功达的作风问题批判和揭发运动。意志消沉的谭功达在此过程中已经稀里糊涂地与乡下泼妇张金芳结成了夫妻。
在谭功达的情感心理过程中,每一个漂亮的女人似乎都让他心动,都可能成为他的结婚对象,但因为花痴和条件的自卑,每一个又都游移不定;但披金拣沙中,姚佩佩在无意识中成为心灵深入的“知心人”,天真的姚佩佩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身怀幻灭和危机感,尽管表面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在一种无知的氛围中,也对谭功达产生了一种同情式的情愫。可以说,谭功达被蒙在一个骗局里,姚佩佩是这个骗局中更无知的那个人。无知的人对无知中的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就像是傻和善良共同的那一部分被激发出来并自然地黏合。姚佩佩也出自自然的感觉向谭功达发出几次暗示,可惜糊涂的谭功达已经难以脱身。
而在此时,主动辞职的姚佩佩却已经被扔进另一个陷阱。因为第一次在大会上相见便被金玉看中,阴谋集团中的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自觉地开展了为金玉的色欲套捕金丝雀的秘密计划。尽管姚佩佩早已有所警觉,并在事发之时表现出为了抗拒不惜与姨妈姨夫决裂的姿态,然而千防万防却陷入了患难之交汤碧云的计谋之中。姚佩佩本已判断出“如果轻信(汤碧云),说不定哪天就被你出卖了”的可能,但终究心性善良,被骗进了钱大钧与汤碧云偷情的那个薛举人的古宅,即p270-271的那个阴线的迷奸场景。 可以说,《山河入梦》中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女青年,都有一种傻气的天真善良与意志薄弱,这种性格特征既让她们对性行为(或那一层膜)保持警惕和害羞,又极容易在被攻破之后放开一切;既温柔善良,又极容易在遭到凌辱之后不敢反击反而变成冷血的刽子手。
在格非的小说中,总是包含着神秘、宿命的成分和想象,同时,从细小的行为、想法到整个的命运又时刻保持着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性。又仿佛人物的某一个细小行为都可能牵动命运的骨架。 姚佩佩被迷奸之后醒来,对于刺不刺金玉的脸(显然她本没打算杀人)有所犹豫,甚至后来在通信中也对谭功达表明,也许当初不如屈从甚至迎合,就能避免死亡的厄运。
这里显露出格非的一种命运观:生命中有什么价值是值得维护的,有什么理想是值得以死捍卫的,也许没有,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虚无。 这种虚无观大概也正是引发“行为—命运”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根本原因。
人不惜命士不惜死,事情就会变得很可怕。但死命总得献身于某种事物,那就是改造天下的一种乌托邦的执念。尽管格非后来不希望被贴上乌托邦这个变了味的标签。这种价值观几乎成了格非所有小说的底色。
从这里开始,小说似乎没有了现实的舞台,或者格非不想让主人公在待在污浊的县城(正如不想让人物过度地陷在时代政治的泥淖中而牵扯出更明显的情感心理世界——在小说中,政治应当永远是背景,否则就是糟糕的或不是小说),于是,在姚佩佩开始逃亡的时候,谭功达被调到共产主义桃花源的花家舍人民公社。
然而,有着共产主义完美图景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在格非的笔下显得极为可疑。良田碧波、平均分配、民风醇和、丰衣足食、民主评议,甚至劳动不需要监督制度,让当初谭功达治下的梅县相形见绌;可怕的是,这里没有惩罚措施,人人心中都想着公社制度,都避免犯罪,人人是组织,人人是书记郭从年;更可怕的是,这里有一个101组织,它保持着和善的姿态,构成透明的、无处不在的监视网,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逃不出它的眼睛。于是,谭功达和小韶之间的交往交流,谭功达所读到的姚佩佩在逃亡途中的每一封信,都被潜藏在身边的驼背老头八斤(其实就是郭从年)所掌握。
随着在那张地图上,姚佩佩的逃亡路线画成一个圆圈而即将回到普济的原点,谭功达的命运透明了,姚佩佩的死期也到了。
正像一开始所言,比起格非惯有的繁复、精密结构,《山河入梦》实在不算波澜起伏。不考虑那些肮脏的政局气候和阴谋的话,单一、乏味、平庸的人物命运似乎映照了社会主义人性和艺术的单一、乏味、平庸,以及渗透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扭扭捏捏、诲淫诲盗的道德感和性观念(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最丑恶和敏感的部分),这可说是时代写照。问题在于,在三、四部分的转换中,格非时如何将一部“政治爱情小说”写成一部“1984”的?
我认为,在这里,格非没能跳开创作意图的先入为主。他希望将从晚清大同、桃花源、花家舍的那种理想基因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第三部《春尽江南》。尽管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乌托邦,但它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实在是太彻底了,那是一个大时代里整架机器的意志,那是没有灵魂的乌托邦。于是,花家舍里的人们呈现出个个良民、面目模糊、集体幸福的影像,尽管那是虚幻的,虚无的。
101这个符号,既是象征,又不是象征,因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这个幽灵同样附在了中国的土地上,附在花家舍的每个人、每寸土地上。
《山河入梦》读后感(十):不梦闲人唯梦君
马不停蹄地追第二部《山河入梦》,相比较而言,这是最为沉重悲情,也是细思极恐的一部 。
在那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关于花家舍,关于桃源梦,很多细节都细思极恐。谭功达终其一生都在为梅县构思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花家舍的模式却让人不寒而栗。
姚佩佩的人生悲剧不在自己,香消玉殒,让人着实心疼,她与谭功达彼此相爱,从未告白,这原本是最美好的一种爱情,却在病态的社会里得不到善终。
紫云英从未远去,也从未出现。